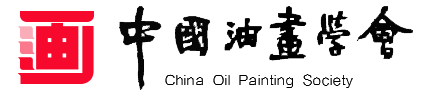沈行工
| 现任: |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常务理事 |
|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 |
|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摘要]刘海粟先生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更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华的杰出画家。他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全面引进及扎根本土的艰巨事业中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领域中的探索勇气和创新精神使他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气派。本文分析了海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中国气派形成的时代背景、作者经历等诸种因素,还就作品的题材选择、表现形式及艺术语言等方面较为深入地阐释了海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风格特色。
[关键词]中国气派 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 民族化
[中国分类号] J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75(2003)01?0013?06
1979年的秋天,刘海粟先生在南京画梅园新村,以实地写生的方式完成了一幅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我有幸在旁观摩了这次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写生的整个过程,深受教益,至今铭记不忘。近日重读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回忆起当年的观画情景,感触良多。海粟先生当时已年过八旬,面对将近一米见方的画幅挥笔纵横,不辞辛劳地站了几个半天,如此的热情和执着令我们这些后生钦佩不已。写生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独到的绘画处理手法给予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得先生在梅园的庭院中取景时,特意选择了一个可以将两棵青松与房舍同时画进画面的角度。起笔时先生是以圆头笔饱蘸普蓝与赭石直接勾画树木与房屋的轮廓,用笔沉稳果断、线条朴拙粗放,有时他笔锋一转,自下而上地逆行走笔,色线更显得滞重遒劲,生涩之中透出力度。随后的铺色,先生则常以几乎未经调和的饱和色彩堆积而上,绿叶中透着红瓦,以强烈的补色对比,交相辉映。由于先生用色华滋润厚,笔触灵动奔放,整个画面有一种纷繁斑驳的丰富感和充溢着生机的蓬勃生息。
说实话,海粟先生作画的手法当时的确让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学院画风熏染出来的学生眼前一亮。相对于那种讲求明暗块面造型、自 然光色关系的写生方法而言,海粟先生的画法无疑是更具有主观表现性和个性特色。后来有机会更多地学习观摩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有了深一层的领悟。每次站在先生的画作前,总会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气势,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派。应当说,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风格既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学养与个性的自然流露和映现,也是他长期以来不懈追求民族精神内涵的结晶。海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是具有中国气派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
海粟先生学贯中西,国画、书法、诗词及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四个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而作为中国最早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之一,他在漫长的艺术人生中始终坚持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在前辈大家中历时最久,同时也是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这一领域中最具探索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开拓者。有学者认为:“海粟老人作为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最能代表他自己,也最能说明他一生。”可以这样说,海粟先生不仅是近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更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华的杰出艺术家,他在将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艺术全面引进并扎根本土的艰巨工程中,倾注了毕生的心力,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绩。
说起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中国气派,人们一定会联想起一度曾在国内美术界备受关注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民族化”这一话题。尽管长久以来画家、学者各抒己见,观点不一,甚至对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民族化”这一提法本身也存有疑议,但论及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中国气派那几乎一致地肯定,中国人画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要有中国气派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在实践中如何真正做到这一点则决非轻而易举。海粟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谈到:“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民族化”的提法是近三十年的事;我们追求贯通中西的创作方法却要早得多”。事实正是这样,海粟先生为此数千年如一日,身体力行,孜孜以求。他曾充满自信地宣称:“(要使)中西绘画的精华,在我的创作中得到完美的统一。”
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功底,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以及超凡的才质和创造力是海粟先生实现自己宏大抱负的前提。海粟先生家学渊源,又经名师指点,得到过象康有为这样的国学大师的亲自教诲,因此有着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青年时代的海粟先生在上海建立美术学校的创举使人们对他的胆魄深为赞佩,这一所中国最早传授欧洲绘画艺术的学校吸引了众多有志于此的莘莘学子。事业有成之后的海粟先生毫无松懈与停顿,继二十年代东渡日本之后,又于1929年?1935年期间两次赴欧考察。除讲学、办展等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外,更重要的工作便是遍访欧洲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追根寻源,深入研究欧洲传统绘画精萃。他曾多次去罗浮宫临摹大师巨作,仰观俯察,悉心钻研;同时他也频繁接触新兴画派的画家与作品,广交同道,博采众长。
如果说,海粟先生的艺术观和绘画美学思想在青年时代已基本确立,那么两次欧游则使之更为坚定与成熟。强调艺术应表现人的情感与个性,应摆脱模仿,根檀创造,力求做到古今中外兼容并蓄、融会贯通。这些主张与见解对于他而言已成为艺术人生中的不变信念了。他曾说过:“画之真义,在表现人格与人的生命,非徒囿广视觉,外鹜于色彩形象者。故
画象乃表现,而非再现也,是造形而非摹形也。”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既要有历史眼光,纵观上下二千年的画论画迹,又要有囊括中外的世界眼光,凡属健康向上可以吸收的东西,都要拿过来,经过冶炼升华,化作我们民族艺术的血肉。对古人和外国人都要不亢不卑,冷静客观。要厚积薄发,游刃有余。‘随心所欲,不逾矩’,达到自由和必然统一的境界。”正是这样的艺术观和美学思想,为海粟先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中国气派奠定了基石。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海粟先生旅欧期间正值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方兴未艾,各种革新画派纷纷涌现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当时的他敏锐而欣喜地接受着这些新鲜的观点和主张,由衷地赞赏着自印象主义起始,经历后印象主义直至野兽主义、表现主义这期间诸位大师的绘画艺术。其中对他影响特别大的应当说是后印象主义的塞尚、凡高和高更这三位杰出画家。这很自然,对于一位一向崇奉石涛、八大,致力于传统艺术推陈出新的中国画家来说,后印象主义画家们所做的一切恰恰与他自己的追求探索不谋而合。显而易见,海粟先生之所以不为欧洲的学院主义和自然主义画风所动,偏偏钟情于新兴画派的艺术,决非偶然。这是由于从后印象主义开启的现代主义诸流派有着这样一个不约而同的基本共识,即认为绘画不应停留在自然形态的视觉经验阶段,仅仅满足于对客观物象的再现,而应更为注重内心情感的表现,使艺术家的模仿冲动转向创作冲动,从而采用主观的个性化的造型手法。形成这些艺术观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须在此一一赘述,其中有一点却是十分重要值得一提的,那就是这些欧洲艺术家从东方艺术中受到的启迪。的确,诸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形写神”、“遗貌取神”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画论中卓越见解,原本强调的就是艺术作品中的情感价值和作者的主观创造性。正是由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海粟先生从这种东西方思想文化撞击与交汇中悟出了自己的绘画艺术发展之路。
当我们纵观海粟先生一生中各个时期的绘画作品,不难发觉一种独特的审美取向始终贯穿其中,这种不拘于客观事物表象描摹而着力抒写个人主观感受的创作观念,在他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中是通过富于表现性的艺术语言来体现的。海粟先生曾经对“再现”与“表现”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反映方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这样说:“在绘画中,‘再现’与‘表现’不同,‘再现’是由外而内的接触;‘表现’是由内而外的开拓”。“艺术家种种的印象,通过心灵的耘酿,用感人的艺术形式呈示出一个新的世界来,这便是‘表现’。”海粟先生认为这两者实际上标明了两种不同的艺术道路,该走哪条路?“我也未敢断言”,海粟先生说得意味深长,但很清楚,他的作品本身就是选择的最好表白。
在讨论“再现”与“表现”的不同含义时,我们会很自然地涉及到表现主义或表现派这样的概念。如果我们不是把绘画中的表现主义仅仅看成历史上某个特定画派的名称的话,那么它也就应当同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这些词汇一样,是在表明着一种艺术的创作观念和美学取向。就这层意义而言,我认为刘海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可以称之为中国最早的表现主义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
令我为之惊叹的是,即使是海粟先生最早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已具有那种表现性极强的艺术风格特征。比如作于1921年的《北京雍和宫》、作于1922年的《北京前门》以及作于1925年的《南京夫子庙》等。从这些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删繁就简、信笔驰骋、直抒胸臆的作画风格,其实也正是海粟先生热烈而豪放的性情的真实写照。所以蔡元培先生在介绍海粟先生那一时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时,就非常准确地指出:“他的个性是十分强烈,在他的作品里处处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色彩和线条都有强烈的表现,色彩上常用极反照的两种调子互相结构起来,线条也是很单纯很生动的样子,和那细纤女性的技巧主义是完全不同。”
艺术贵在真诚,真诚的艺术是动人的。海粟先生早期的那些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直至现在仍然深深地吸引着我。依我本人研读海粟先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心得而言,我认为,虽然海粟先生在长达近八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来加以研究,但其总体的绘画语言特色却是相当地鲜明而联贯一致,构成了一种极具个性的、表现性很强的艺术风格。即使是在欧游之后他的作品看上去“其表愈纵恣,其里愈谨严”,然而“彼邦美术家始亦知海粟为海粟,而非所谓西洋画家”。(见陆费达《海粟之画》)。至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的艺术高峰期,也是他画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最多的时期,作品中这种“经过心灵的酝酿,智力的综合,表现出来”的情感色彩便愈加浓郁深沉,夺目闪光。
当我们试图较为全面地论述海粟先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中国气派时,必然还需要从上述有关艺术观和美学思想这一层面,继续深入分析海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及作画技法等各个层面的特点。众所周知,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作品的题材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种合适的题材的选择往往为作者发挥其潜在的艺术才质提供了施展的天地。我们纵览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可以看到除了访欧期间在国外的旅行写生外,绝大部分作品是以祖国各地山川风光为题材的风景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静物花卉及人物题材较为少见。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炽热之情自不待言,海粟先生更从中华大地的这些景物中感受到了民族的魂魄与精神。他说:“我画八达岭长城很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豪感。利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色块的体积感、雕塑感去造型,……因为他的外貌,便是民族化的东西”。顺着先生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他对风景题材的选择显然有着人文意义上的深层考虑。
在海粟先生看来,不论是三川五岳还是江南塞北,显现的都是中华大地所特有的自然形态,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在这块热土上生存、劳动与延续,因此,一山一水、一石一木无不牵动着民族的情感。在海粟先生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最令世人称奇的是,海粟先生曾十次登临黄山,而于1988年第十次上黄山时,先生已是93岁的耄耋老人了。黄山是中华奇观,天下绝秀,确实气象万千,海粟先生一直称之为自己的“良师益友”。黄山的雄奇壮观给予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就某种意义而言,黄山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自然风貌也触发了他对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民族化的思索。以黄山为题材的国画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是他的作品中数量最多的部分。由于年代久远前几次上黄山所作的绘画多已散失不见了,仅1954年六上黄山的写生作品保存较完全,有不少佳作,其中的《黄山温泉》是他本人认为画得较为抒情与细腻的作品。而画得最为精彩最具气势的还是1981年之后的八上、九上、十上黄山的作品。像《西海门:隆观》、《黄山云海》(1981年),《白龙潭》、《雾笼北海》(1982年),以及1988年十上黄山所作的《重岩叠峰》、《始信峰晴翠》、《西海晚晴》和《石海云雾》等等。这些作品几乎将黄山的晴岚烟雨,千峰万嶂尽收画中。海粟先生借黄山之奇峻以笔底波澜倾抒胸中豪气;尤其是十上黄山的几幅作品,画得极为简洁生动,较之以前的作品更有一种飘逸轻快的笔致,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几幅作品。使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作品竟是一位九十三岁的老人在高山之巅实地写生完成的!
除了黄山之外,桂林、阳朔的漓江,杭州的西湖以及庐山、泰山等等都是海粟先生喜爱的风景题材。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画面上直接题写诗词是海粟先生的一种新尝试,他在1978年画的《山色翠浮空》、《阳朔》和《伏波山写漓江》这几幅作品中均有题词。其中《伏波山写漓江》一画中,上半部分的天空未着颜色,在画布上题有大段诗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剪取漓江清黛,妆点神州风貌,留待后人宗。”这既是老人触景生情的心声,也表明了对自己所作的创新尝试的信念。
海粟先生的风景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还包括一部分以各地的名胜古迹及名人故居为题材的作品。上文提到的《北京雍和宫》、《南京夫子庙》、《北京前门》以及《苏堤夜月》、《三潭映月》等是他早期的作品,后来则有《八达岭长城》、《北京天坛》、《白塔》、《甲秀楼》和《南京梅园新村》、《孙中山故居》、《遵义会议会址》等作品。名胜古迹作为千百年华夏历史的见证其文化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有些建筑本身也往往体现着本民族的审美意趣。海粟先生在画这些景物时通常并不在意表象的如实再现,而更注重其内在的象征意义。每当画到革命前辈的故居时,老人的景仰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谈到《南京梅园新村》这幅画时说:“我要用国画味很浓的笔触,把周总理的精神画出来,要使人回想不断”。还在画上题写了”;吐志劲松千秋在”的诗句。1982年海粟先生在广东画《孙中山故居》一画时,在构图上特意把中山先生手植的酸子树安排在画面的突出位置“作为历史见证的那棵历经风暴,宛如昂首卧龙斜云欲飞的百年老树,与故居殷红的门墙相辉映,庄丽肃穆,谱写了对伟大革命先行者勋业的颂歌。”(见谢海燕教授撰写的《刘海粟》画册前言。)
在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中虽没有那种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场景的情节性、主题性的作品,但他始终非常关心祖国的建设与发展,努力以自己的作品来赞颂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他在不同的时期所作的《太湖工人疗养院》、《梅山水库》、《佛子岭水库雪景》、《上海庙会》、《外滩风景》、《苏州河夜景》及《广东大鹏湾》、《头头湾望澳门》等作品表达了老人面对日新月异的祖国面貌的由衷喜悦,也寄托了对于人民美好生活前景的祝福。
同样,甚至从海粟先生静物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题材选择上也能对他的达观向上的昂扬个性感知一二。他最爱画的花卉是向日葵和鸡冠花,这两种花都具有花型丰满、枝叶茁壮、色泽浓艳的特点。前者的亮黄、后者的深红,非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颜料的饱和度无以传达出色彩的庄丽之美。海粟先生早年旅欧期间便曾在法国和比利时分别画过葵花,从那两幅作品的构图、运笔可以看到凡高的作品对他的影响。而作于1961年的《最爱无花不是红》和1969年的《向日葵》则已然完全是他个人的独特风格了。此后他还曾一再以这两种花为题材,画得有声有色。
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是艺术家的创作初衷。一位优秀的画家在作画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寻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表达内心情感的题材与形式。我们可以看到,海粟先生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题材上的选择与他本人的国画作品题材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极为相似的方面,这正是一位性情率真、内外如一的艺术家出自内心的真诚表露。当然,海粟先生绘画作品题材方面的特点,除了个性的原因之外,他显然也受到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诸画派的影响。就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题材而言,后者的影响是千分明显的。印象派、后印象派乃至野兽派等画派的绘画作品在题材上与此前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有着很大的差异,这说明由于创作观念的改变而导致的绘画表现形式上的革新,同时必然伴随着作品题材重心的转移。
应当承认,作品的题材虽然对绘画作品风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有时并非一定是实质性的、根本性的。突显画家作品风格面貌的更关键的因素往往是作者在运用绘画艺术语言方向的特点。海粟先生在追求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民族气派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曾对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表现形式、艺术语言作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种探索不应停留在浅层次的阶段,不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嫁接与拼凑,他曾说过:“正如章回体不等于小说的民族特色一样,单线平涂不等于民族化的绘画。”因此,在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显现出的中国民族气派实际上是一种经过冶炼熔铸而成的内在气质。
海粟先生一直认为,中国画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主要是工具的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同,就艺术传达情感的意义而言应当是殊途同归的。他善于从中西绘画中撷取各自所长,有意识地加以融合与强化,来逐步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特色。前面曾提到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与国画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艺术语言这一层面上,这种一致,尤其是对于画家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可以从海粟先生在绘画的构图、色彩、造型、线条、笔触等等诸种形式元素方面看到这种一致性。依我所见,其中最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线条的运用。
线条作为绘画艺术中最重要的形式元素之一,不仅在再现客观对象方面具有明确的、生动的造型意义,而且在表达作者主观情感方面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线条是运笔过程的记录,这种记录常常将作者作画时的心路历程展现无遗,由此而可能成为画面上最动人心弦的艺术语言。绘画中的点、线、面都是作者运用笔触而咸的不同形态。应当说,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的笔触有着隐性和显性的区别,某些古典画风的作品画面光洁平滑,几乎难以看出笔触的痕迹,而另外一些作品中则笔触与肌理的效果十分明显醒目。如果说印象派画家尤其是莫奈的散涂式笔触经常呈现为点状的,那么塞尚那样斜扫式的笔触就可称之为块面状的,而凡高的笔触则更接近于线形的。同时,在很多画家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绵延流畅的长线条被用于塑造形体,表情达意。
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中西画家对于线条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在文艺复兴前期的近代西方绘画的不少作品中线条也是十分重要的艺术语言,但就总体而言,西方绘画从未有如中国传统绘画那样重视与强调线条自身的表现价值,这与中国画中“书画同源”的传统绘画观念是紧密相关的。海粟先生的书法与绘画齐名,早已广为人知。他的书法有碑学的深厚功底,且正、草、隶、篆莫不兼善,因此他落笔见力、留痕有韵。这对于他的绘画包括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线条的运用有着直接的影响,“以书入画”也就必然是海粟先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最为突出的风格特点之一。
人们知道,传统水墨画一向十分讲究“见笔”,在生宣纸上作画可说是“落笔无悔”。很多情况下,画中的线条最初的也就是最终的,不太可能多次重复或更改,这是水墨画的突出特点之一。然而如果仔细研究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将会发现他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中的线条运用有着类似的特点。一般说来,用线来勾画轮廓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是正常的绘画步骤,但由于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颜料的粘稠度高,覆盖力强,这种轮廓线很少被一直保持到最后。海粟先生作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常常一开始勾勒轮廓时便非常讲究用笔,线条显得生动有力,而为了保持这种最初的线条的表现性,他在填色时会有意无意地留有空白,露出布面底子,因为如果线条被周围的颜色遮盖,那么原来那种线条的气韵就不连贯了。这种情况在他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风景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树木枝干,房屋建筑一旦以线勾写出来,便努力保持着起初的韵味。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幅作于1977年的《杜鹃花》这幅画中花卉与枝叶画的飘洒灵动,如草书一般,而勾勒红木花几的线条则遒劲滞重“力透纸背”,完全是篆书的风范。
海粟先生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的线与西方画家的线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前面说的特点之外,他用笔喜用中锋,无论是在空白的画布上直接抒写,或者是在多遍色层上再次勾画,他总是力避纤弱与轻浮,线条宁粗勿细,字涩勿滑,宁拙勿巧。作于1957年的《复兴中路雪霁》是一幅多层画法的佳作,画面上冬日的枯枝、行人与积雪相互叠合,以交错用笔的方式作成,产生了一种斑驳丰富、浑朴厚重的视觉效果。另外象《存天阁积雪》、《桂林花桥》、《蠡园晚霞》等作品在用线方面均各有妙处,耐人寻味。及至海粟先生1988年十上黄山所作几幅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则可能已是先生最后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了。这些作品画面气势磅礴、笔姿自如、线条坚韧,真可谓:“惊蛇枯藤,随形变幻,如有排云裂阵之势,龙蜒凤舞之形。”作品充分显示了一位九十三岁老人顽强的生命力量。
与其他画种相比,色彩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的重要意义是无可置疑的。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在色彩运用方面同样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特色。他曾潜心研究过欧洲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色彩奥秘,尤其倾心于塞尚、凡高以及马蒂斯等大师的色彩处理手法。他洞悉中西绘画在色彩表现上的巨大差异,因而立足于从更宽广的视野中体察民族文化中的色彩美学倾向,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取精用宏,融会贯通。海粟先生非常注重色彩的表现性,对于不同色相、不同明度、纯度和冷暖的色彩各自的情感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一般说来,在绘画的形式语言中,形体可以提供确定的式样信息,而色彩更倾向于表情的传达。色彩是较之形体更具有可变性和自由度的形式元素。海粟先生认为,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色彩的运用上强调作者主观感受的充分表现是十分必要的。在他以黄山为题材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在色彩上“借题发挥”的。事实上,从自然景观本身来看,黄山的晴岚烟雨、千姿百态、变幻莫测为绘画色彩运用的灵活多变提供了极佳的客观条件,因而当我们看到海粟先生笔下的黄山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有着如此绚丽璀璨的色彩交响效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作于1981年的《西海门壮观》、《莲花峰夕照》、作于1982年的《黄山云海》、《光明顶看始信峰》以及作于1988年的《始信峰晴翠》、《西海晚晴》和《石海云雾》等,均为在色彩运用方面最为成功的作品。
海粟先生喜爱用对比性强的色彩来表达自己的激情,红与绿、棕与蓝、橙与紫等等具有补色倾向的色彩并置常常成为他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的主色调。特别是红与绿的对比,他用得最多,也用的最为精彩。《南京梅园新村》与《孙中山故居》是其中的代表作,两幅作品虽同为红绿相映的对比性色调,然而其间亦有微妙的区别,前者的红瓦色泽温暖,近乎朱红;后者的红墙则稍许偏冷,类似玫瑰色。前者画面上有较多的赭石色陪衬朱红,后者则有群青烘托玫瑰色,从而使两幅画各自呈现不同的色彩调性。在海粟先生晚年所作的《福州鼓山》一画中,绿树簇拥着古庙,构图充实饱满,加之庙墙大块的砖红色彩,整个画面显得雍容而富丽。应当说,红与绿是人们最为常见和熟悉的一组对比色彩,它们处于色环的两极,呈互补色的关系,因此对比强度最大,色泽也最为浓艳。在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和传统艺术中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一种色彩组合的形式。从中国古典建筑的色彩配置方式中固然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而在民间艺术和戏曲艺术中涉及到色彩处理时更是经常会看到红与绿对比的广泛运用。海粟先生曾多次提到京剧中的关公戏,他不仅对京剧艺术的表演赞不绝口,也十分欣赏欣赏京剧的服装道具设计。比如关羽的枣红色面容与翠绿色战袍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就具有一种特有的瑰丽与庄重,有很强的视觉效果。因此,也可以说红与绿的对比是最为通俗、最为人们喜爱、也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色彩处理手法。
“大红大绿,亦绮亦庄,神与腕合,古翥今翔”,这是海粟先生在一幅画上的题句。确切地说,这句话并不仅仅是表达了作者对于绘画色彩运用的一种见解,而更是一种博古通今、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艺术观的宣示。海粟先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艺术风貌是他的品格,学养与艺术观的综合体现。论述海粟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中国气派,或许只是涉及了海粟先生绘画艺术的一个方面,尚有多个方面的课题需要作深入的研讨。从总体上看,海粟先生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是具有雄肆豪迈气概的一种黄钟大吕式的作品,是一种注重主观情感表现而不拘于再现客观表象的绘画性很强的作品,而令我内心最为钦佩的一点则是海粟先生作品中那种不事雕饰、浑然天成的画风,因为这说明了真正的艺术一定是真诚的、自然的。
沈行工
(《美术与设计》2003年第1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