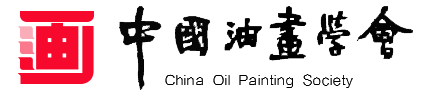尚扬
| 现任: |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副主席 |
|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 |
| 中国美协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艺委会委员 |
尚扬在附中和大学的学习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艺术的基本看法,而将这些看法转变成成熟的艺术作品,却又等了十多年,从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开始,到1979年重新考入湖北艺术学院做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研究生。大学毕业以后的十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谓“轰轰烈烈”的日子,但对于尚扬,那可是一段真正寂寞的日子。大学毕业后的十四年间,他没有可能去画自己想画的画,对于自己曾经深爱和深究过的艺术,有时竟是如此遥远和不可企及。而极端的革命岁月,主宰自己命运的想法,比起以前来,倒更接近疯狂。
这是尚扬一段沉默的日子,一段自我退隐的日子,一段自我放逐的日子。
那些成就了大事业的人,有不少都经历过和尚扬类似的日子。可正是在这样一段堪称寂寞的日子里,尚扬煅造了自己的艺术思想,把此前所学的一切,人生的和艺术的,来了一次漫长的反思。
准确地说,大学毕业以后的尚扬,对于热闹的美术界来说,是真正的异类,真正的边缘人物,甚至是个与美术无关的陌路人。
他的同学们多少都已经或正在辉煌,而他却站在一旁,默然无语,像个满足现状的小职员,只是吃饭睡觉过日子。
这是一种长期反思、反叛和怀疑的结果,是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不肯轻易就范但又一时找不到合适出路的天涯孤客。
1973年的秋天,他和张琪敏结婚。1975年的夏天,他们的女儿尚予诞生,这是他最重要的生命果实。
其实,在那一段日子里,尚扬想得很多,也想得很深。并不是说在那个寂寞的年代,就已经完全形成了后来的艺术思想,也不能说以后的许多思路,和那特殊的岁月无关。思想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混合着,既塑造着日渐蓬勃的生命,也构成了人生回忆的崭新内容。
他缓缓说道: “我对待艺术有些自己特殊的习惯,不想画画时,我绝不去画画,我情愿去漫游。另外,我不喜欢画的东西,我绝不画它。
“我从很早开始,就形成一些自己非常个人化的标准。画速写,不粗糙不画,非要画得粗糙不可。那原因大概是因为我有很长时间关注岩画,被岩画的粗糙所感动。我对那种效果简直是痴迷,甚至认为,不粗糙就不能成为好画。
“同时,我喜欢观看而不喜欢临摹。我一直将中国古代艺术作为我自己日常浏览的对象,到现在我的画室总是摆放着董其昌和元四家的画集,以及其他种种自己想随时可以翻看到的各种有关中国文化的画册。
“所幸在‘文革’前,我就从印刷品上收集到许多古今中外我认为最为杰出的艺术作品,将它们制成了一套自己可以随身带着随时浏览的图片。即使在鄂西南的大山中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带着它。只要没有人,我就拿出来观看。这些东西伴随我度过了空白的十四年。
“八岁的时候,父亲让我临字帖,他看我长得单薄,让我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我就横一笔竖一画地临起来了。后来发现《玄秘塔》、颜、柳、欧、苏都远不如二王的字,二王的字比较简洁。但后来,我不临帖了,偶然中发现了北碑,觉得碑比帖要精彩得多,精彩就精彩在那种石味和损毁的痕迹,苍劲而笨拙,不巧不油滑。以后才知道碑帖之间,原来还有一场重大的争论。但是,对碑的热爱却至今未变。
“我从小就喜欢东看西看,我的学习方式一直就是综合的,是典型的拿来主义。小时在父亲的影响下,喜欢看古画,可长大后,在学院里学习,却发现老师教的与以前看的不一样。这是一个奇特的发现。大学时,老师说画线要平直,不能毛糙。可我小时看展子虔的《游春图》,那里头的线就既不平也不直,而是极其富有韵味。为什么偏偏老师要求我们画平直的线?我很快就不喜欢那平直的线了,我以为那玩艺油头滑脑的。其实,我很能控制线条,附中时就有不少同学认为我应该选择国画。可是他们不知道,线条不是我的目标,我不喜欢仅仅有线条或用笔。我对材料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笔墨的兴趣,我不会去学国画。但是,在我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里,我就明显地融合了书画的线条感,也特别注意用笔。当然,这还是一种技巧上的综合。好的综合是风格性的,是对各种观念重新组合的结果。
“八十年代,我结束了沉默期,但这时碰到的却是个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什么都是以西方马首是瞻。后来去了趟德国,看了许多西方现代派的东西,知道这中心主义问题太严重,自己不管如何有创造性,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冲击之下,始终是边缘的,在1993年的最后一天,文化学者余虹和我做了一次长谈,由他撰写了一篇我们两人的对话,题目叫‘反二十世纪’。
“反二十世纪的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反二十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反在这种中心主义之下的文化霸权,反向它们靠拢,向它们献媚。
“我还想,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不仅要有中国人的观点,而且这观点还必须是当下的。我一生中经历了多少风格,同样,我也目睹了太多的风格,像过眼烟云那样,在历史上一晃而过。历史只留住那些深思熟虑的作品,只留住那些回答当代问题的作品。
“有学养、有当下的针对性、有视觉冲击力,这是三个相悖的目标。我总想着如何在我的艺术中把它们统合起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一个独立于我而存在的生命。我知道我的希望在很长时间里不合时宜,我更知道如何寻找到表达这三个目标的形式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1990年到1991年,我开始了一种综合风格的工作。我明白,在现代主义已经形同末路的现在,只有一种综合才能表达一个当代人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文化际遇,以及他们的不安与探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中国也正在走向这个不可避免的综合的时代。”
尚扬说到这里就打住了。我惊讶于他的坦率,更惊讶于他那平凡却奇特的经历。他居然有一长段时间不画画。他不想画画,甚至不想从事艺术。尚扬对艺术太认真,太执着,太较真。他不认同时代,所以他就沉默。
我想起了鲁迅的名言: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尚扬没有灭亡,他爆发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八十年代,对于将近四十的尚扬来说,是他人生当中最为美好的岁月。他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艺术上的攀登。他以敏锐而不可思议的冲击力,给那个渴望新生、渴望变革的年代描上了浓重的一笔。他积四十年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思考,积四十年的全部热情,感染了那个创新与守旧、传统与反叛、开放与封闭并存的大起大伏的日子。尚扬,以一种让同代人惊讶、让后辈人仰慕的姿态,出现在错综复杂的中国艺术界。尚扬,在那个年代成了一种自我超越的标志,一个不停地反叛的形象。而这一切,是从黄河边上开始的。
八十年代的艺术,不管是电影还是文学,都离不开对黄河的思考。成也在这里,败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