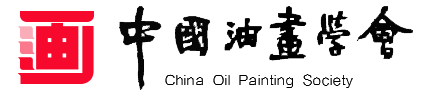尚扬
| 现任: |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副主席 |
|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 |
| 中国美协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艺委会委员 |
从1958年到1981年,整整二十三年。当年那个刚刚读上附中、对艺术充满幻想的少年,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经历了无数的运动,正常甚至平常地生活了过来。直到现在,尚扬才开始觉得有一种压抑了二十三年,应该说不止二十三年的情感升腾起来,要把当年那一声声激越的秦腔变成个人的视觉世界,让众人惊叹其中的高贵和力量。
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尚扬前后四次去黄土高原。二十多年来,不管尚扬在艺术风格与追求上如何地大起大落,但是,他在黄土高原所激发出来的那份情感与飘泊的体验,却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的时期浮泛上来,从而构成了新风格的基础。黄土高原似乎成了他的一个精神领地,一个洗净自身负累的一个场所。当年那张糊在泥墙上画就的大型素描稿《黄河船夫》,几经磨难,多次残损,却仍然被小心地珍藏着。有知心朋友来访,或与友人谈起当年的艺术,他就会把素描拿出来,边比划着上面的形象,边总结八十年代初那场“文革”后的思想运动所带来的震撼。
九十年代初,距离尚扬第一次去黄土高原已经十年以后了,在给好友张士增的水墨画集写的文章里,他对八十年代有过一个简括的总结,认为“那是一个粗糙而匆忙的时期。”今天,谁也不否认尚扬讲的是一句公道的话。
正是在那个匆忙而粗糙的变革当中,尚扬从黄土高原寻找到了自己艺术灵魂的原生地。
1985年,在一封写给着名艺术家周韶华的信中,尚扬谈到了他自己的思考:
“几次黄河和黄土高原之行,使我开始悟出一些道理。我之所往,是为找一条自己要走的路口;我之所取,是为寻求一个民族文化生成的基因,找到一个人与自然……的契合之点。”
那么,这个“契合之点”是什么呢?在那篇谈及自己创作《黄河船夫》的文章中,尚扬写到:
“这些船夫们的无可羁縻的气概是这样地震撼了我。在这落寞的黄河一隅,我真实贴切地感受到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种巨大力量。在船夫们的与黄河不足较比的身躯里,却透露出一种征服自然的伟大。”
处在那个年月的思潮当中的尚扬,在黄河边上所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带有象征色彩的对比情景,这情景颇能表达一种对民族性的复杂思考,而正是这种复杂的、却又无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的思考,准确地反映出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总体倾向。恰恰是这样一种总体倾向,促使尚扬对黄河的风情地貌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情感。
这就是在“粗糙而匆忙的时期”,尚扬所怀有的理想,那时他是把个人放在一个大的思想框架里的,他希望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个民族的再生发出艺术家的呼喊。
其实,尚扬的呼喊也是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呼喊。
进入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局面。“伤痕文学”带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波运动,并且马上波及到了美术界。紧接着这一运动而来的,却是两个相异的审美追求,一是艺术上关于“形式美”的广泛讨论,一是由反思“文革”灾难和极左思潮而带出的寻根意识。前者把重点放在艺术本体上,认为艺术本身足以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无须任何强加的内容,相反,那些强加给艺术的政治与社会内容,只能损害艺术本身。显然,这是一种毫无新意的“形式主义”观点,它之所以在那个年代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说到底是对过去几十年整个意识形态忽视甚至贬低纯粹审美的反动。事实上,“形式主义”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包括艺术问题在内,它尤其不能满足人们对社会的反思需求。因此,就在“形式美”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寻根意识就迅猛降临到文学艺术界。在那个“粗糙而匆忙”的年代,人们更愿意思考引起整体灾难后果的原因,追踪背后的思想根源,于是,“寻根意识”开始蔓延了,并迅速在艺术的各个领域体现出来。
有意思的是,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是个形式主义者,而有的人不管如何创新,本质上都是一个主题先行的人,始终让思想大于形式。但是尚扬却巧妙地让这两者统一到了自己的艺术当中。
从思想与审美根源看,“表现与抒情时期”的尚扬是顺从寻根意识的,他甚至主动地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寻求整个民族的文化根基,自觉地为这种意识贡献自己的思考。这个时期的尚扬,作为个体基本上隐藏在以“寻根”为代表的整体思考的框架当中。以“墨实吟”署名的一篇探讨尚扬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的评论指出:
“如果‘西部精神’这一概念可以成立,那么尚扬无疑是探索‘西部精神’的先行者之一。”
作者继续写道:
“面对尚扬的画,我总是被一个问题追逼:他为什么酷爱陕北、黄河、黄土高原?许多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说不清的情绪扰得他心烦意乱,什么都不想画,什么都画不了,线条恍惚,色彩飘浮,每一笔都难以找到它安定的家园?尚扬‘病’了。熟悉他的朋友知道,这简直是一种‘思乡病’。……尚扬画画是‘还乡’。”
显然,作者的意思是说,尚扬还的是“西部精神”这个乡。也就是说,尚扬是在寻根,不过不是他个人之根,而是“民族之根”。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民族文化生成的基因”。作者甚至还把“尚扬黄”这种说法和寻根意识结合起来了:
“尚扬本能地捕捉了这无人的自然,或者说,这融入了自然中的人,并用笔触、构图、色彩,尤其是色彩惊人准确地表现了出来:‘尚扬黄’。这就是黄河源,这就是炎黄子孙生息繁衍的黄土地?人和自然混沌一体。”
作者的解说带有浓厚的八十年代的艺术评论风格。在这里,他还是准确地点出了那一时期尚扬艺术的思想基点。
只是,今天来看那个年代尚扬的艺术,特别结合到他以后的发展,就发现不能用“还乡”这么一种含混的说法来论说了。骨子里面,尚扬始终不脱“形式主义”的趣味,对雅致、拙朴、直观等视觉效果耿耿于怀,至今不忘。同时,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尚扬却又根本瞧不起那些玩弄形式的艺术风格,而念念不忘意识、观念、思想深度等抽象的问题。前一个“尚扬”使艺术家自己终日沉迷在各种“效果”的实验中,极端时不画任何无特殊效果的画;后一个“尚扬”则往往演变成为“哲学家”,把个人的思考强塞进作品里,以致形成了一种略带晦涩的视觉倾向。尚扬在艺术上的双重性,在他一开始显山露水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呈现在一系列的作品中。
尚扬从来就反对“形式主义”,同时他也反对思想等于或大于一切的空洞玄想。表面上看,“黄土高原时期”的尚扬没有脱离当时的思想氛围,愿意自觉地为整个民族的反思努力,并成为美术界这种思潮的一个“先行者”,所以他很快得到了普遍的赞誉与认可。但是,如果愿意深入一些来观察的话,我们还应该看到,尚扬长期的教育和思考促使他不愿意、也不可能成为某一种思潮的俘虏,让个人沉没在整体思考的汪洋大海中难以自拔。
其实,就在那篇自我介绍创作《黄河船夫》的文章中,尚扬除了强调对整体思维的追索外,也流露了对于纯粹绘画的向往。一方面,他表达了对悲怆而苦涩的乐观主义的向往,并让这种思考支配了“黄土高原时期”的艺术家的创作;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又强调了对艺术语言的探求。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写到:
“对于一张画来说,没有适当的技法语言来体现,构想再多也枉然。关于这张画的技法表现,我原意力求在手法上拙朴生涩些,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画看起来十分完整,但刻意求工或甜熟得油滑,往往失去艺术的真率。这使我想到孩子们的画。他们的画总显得那么生气勃勃,往往透露出艺术的天机。相比之下,成人的画是天趣太少了,画什么都准,都精到,却又觉得差些什么。”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立足在八十年代的整体思考的情结中,尚扬也流露出了另一种异样的追求,这种追求注定了他始终会摆脱“表现与抒情时期”的风格倾向。今天来看,多变的尚扬其实一直保留着一种不变的气质。不管是他作为过渡阶段的“沉思与材料时期”,还是后来全面确立自我地位的“符号与象征时期”,都保持着一种不变,那就是艺术家个人的思索品格与高雅气质。我相信尚扬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追求的底蕴是什么。
正因为尚扬“觉得差些什么”,所以,在他功成名就备受赞誉的时候,却陷入了空前的苦思冥想当中,几乎不能自拔。
“尚扬黄”所带来的成功不能安慰这个思索型的艺术家,他的异变呈现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而兴趣点却集中在对肌理的探求上。黄河,这条民族之河显然没有把艺术家完全解放出来;整体性的寻根思维更没有帮助艺术家确立个人的思想坐标。艺术似乎比那激动人心的“尚扬黄”还要多些。“表现与抒情时期”那质朴的西北风光和人文情怀不是画家的最终目标。
那搅动画家思索的动力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