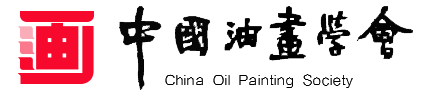闻立鹏
| 现任: |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艺委会委员 |
|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艺术功能多样,总离不开人生的目的。毕加索也曾画过《格尔尼卡》这样重大主题的画。艺术的审美功能是最本质的,无论什么体裁和题材,我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艺术的领域十分广阔,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能穷尽过。各绘画品种之间,甚至各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吸收,存在着更加丰富艺术的可能。我喜爱诗,总想把诗意引入画境;我喜欢音乐,总想追求绘画的音乐美。
艺术的语言丰富多彩,形光色、点线画,不同的观念、构成和风格,使艺术满足着各种不同审美品格与层次的要求。作为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生活中的色彩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感受。我追求色彩语言的魅力。
艺术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客观生活中确实存在无数美好的事物,我不满足于简单地再现。用我的眼睛观察,用我的头脑思考,我追求用自己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诚感受;我追求在用画笔物化自己真诚感受的过程中的新的创造。
像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等一样,技艺美也是艺术美的组成部分。我探索这种新的创作:中动所要求的新技法,我追求这种新技法所表现出的难以言传的美感。
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前进。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丰富、多样。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力求不停顿自己的步伐。
作为一个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我的艺术触角将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探索。我不拒绝西方艺术体系的观念与技巧,无论是古典或现代的,具象或抽象的;我也决不放松对中国东方艺术体系的学习与吸收,无论是传统或民间的。让艺术具有现代的、中国的、个性的素质,这是我心里的目标。
唱出心里的歌
1994年我在个人画展的前言中写过一段话:
我爱山野。苍莽博大的群山,是大地的脊梁,给人以壮伟崇高的美感。
历尽艰辛登临峰顶,脚踏坚硬的岩体,手摸冰冷的青天,极目苍茫,迎风长啸,你能领略到一种宇宙意识,心胸豁然开朗。
我爱岩石。粗犷雄浑的岩石,是崇山峻岭的缩影,是山脉的构架与裸骨,是大山灵魂的象征。山岩的品质感应着耿介坚毅的品格,我常在无言的岩石体会到有情的人生,体验到永恒不屈的生命意识,感受到一种搏击人生的精神升华。
岩石的形态、色彩、体量、材质、肌理中蕴藏着无限的美感,是以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语言抒情明志、表现关与力的极好载体。
我爱大自然,也爱大自然中壮美崇高的一切。辉煌悲壮的秋,迎风挺立的树,奔流直下的飞瀑,常能使我流连忘返,激发起难以抑制的创作欲望与灵感。无论是激情的礼赞,或是低回的咏叹,或是一缕哀思,哪怕只是一声微弱的叹息。我试着用一切能表情达意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语言唱出心里的歌。
转瞬六年过去了,风景画创作已占据我全部的时间。有时我常问自己,为什么这样钟情于大自然,钟情于风景画?为什么面对白桦古松岩石峻岭,总有那么多说不完的心里话?其实这和我70年的生命历程是分不开的。
我出生后就来到就来到青岛,母亲说那时蓝色的大海就在窗下,白天任海风吹抚,晚上伴着涛声入睡,这有节奏的涛声也是襁褓中我的催眠曲。
后来,随父亲回到北平郊外的清华园,远离城市的喧嚣,西山脚下,庭院中的松墙绿草,修竹碧桃,伴我渡过无忧无虑的幼年。
抗战期间,在春城昆明,为防空袭避居农村,白色芬芳的野蔷薇,高大挺拔的尤加利树,碧绿稻田里的点点白鹭,松林中上下跳跃的长尾松鼠……
四季鲜花的乡村田园生活环境,送走了我的童年。
大自然给我无形的美的熏陶,而父亲“诗化生活”、 “诗化家庭”的理念,更使我得到诗和艺术的环境和氛围。中秋月光下村边散步、赏月,冬日银装中踏雪寻梅,床边油灯下讲诗,父亲潜移默化地把孩子们领进了大自然诗的意境,陶:台启迪着我们对大自然美的领悟,营养着我们幼小稚嫩无邪的心灵。 《长恨歌》、《琵琶行》、《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I……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l”当时的孩子们当然还远不能领会诗中的宇宙意识和蒙太奇式的艺术描写手法,可是通过父亲讲解和朗诵,却可以慢慢体会出那自然之美的诗意,那韵律之美的魅力。正是这些诗句成为中介,使我朦朦胧胧地亲和了大自然,滋生出对艺术光照的向往。
我16岁来到了解放区,从此走进了大山的环抱,也开始走进艺术事业的圈子。此后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差不多都是和山川大地农村田野相联系的,土改、行军、 “四清”、下放;开门办学,深入生活,写生采风,艺术考察,更是围着山川大河转,沿着田边地头跑,田园的、旷野的、荒漠的、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自然美,不断地在脑海中浸润着,积淀着,激荡着。
终于,我的心灵好像已经和自然的壮美、自然的伟力难解难分了。
对着高山,对着丛林,对着养育人类的大自然,我越来越敬重、越来越热爱她了。几十年在祖国各地,在世界各国,从天空,从海上,地球村里的壮观美景,以她们的优美与壮丽,以她们的崇高和伟力,给了我最大的审美享受、最丰富的灵感、最旺盛的创作激情。我像一个欠债的人,时时为未能满意地表情达意吐露心声而不安。
于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内心的艺术感受,难以抑制地通过一幅幅风景创作流淌出来。雕塑家刘焕章对我说,“文革”之后他的创作构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地往外蹦,这大概是这一代画家经历苦难压抑后的共同感受。
在我动荡激越的人生旅程中,命运之神似乎使我比同代人更多地承受着心灵的苦痛压抑和沉重。
少年时代父亲遇刺、哥哥垂危、母亲重病的突然降临,给我的心以强烈地撞击,真正体验到悲之痛、愤之力、爱之深、恨之切,在天昏地暗中我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中年时代人生旅途的坎坷颠簸,从座上客到阶下囚,又使心灵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锤炼,体验了崇高、正直、善良的灵魂撞击与抚慰,也见识了丑恶、伪善与卑下的种种表演。于是,渐渐地,在我对自然的亲和体验过程中,;仕美崇高的审美感悟越来越强烈鲜明,触景生情、倾诉真情、抒发胸臆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随着了70年沧桑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增长、思维空间的扩展,我日渐觉得,艺术海洋里的美的形态是极为丰富多样的,体现阳刚之气的壮美、崇高、悲剧……等等,远不是和谐统一的优美一种形态所能包含,当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漂亮”所能替代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优美意境的表现,而更加向往;仕美崇高境界的创造、磅礴力度的表达、人生哲理的思考。
这是我经历的人生道路所形成的、发自内心的情感需求,我的画笔与色彩只能顺应感情的流向涂抹挥洒,情不自禁,别无选择。
日本作家川端康咸说得好, ”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
的确,这是艺术家的理念,是艺术家乐此不疲的兴趣所在,也是艺术家苦苦求索、辛勤劳作的价值所在。
我深切体会到,艺术从发现与感受开始,却不应以临摹与复制告终,艺术贵在有所创造。而这一切,关键在于真情二字,眼睛可以看到形光色,耳朵可以听到各类音响,但眼睛、耳朵也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有用心灵才能感悟大自然的美,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才能回应大自然的倾诉与呼
唤、而自然地流淌出画家的心声。
路正长而生命苦短。向着每天升起的太阳,我将唱着心里的歌,默默地一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