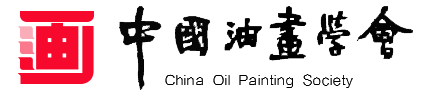詹建俊
| 现任: |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名誉主席 |
| 中国国家画院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院院长 |
詹建俊的创作生涯,似乎可以说是从他描写勘探队员在荒原创业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起家》(1957 年)而“起家”的。这位当时只有26 岁的中央美术学院由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指导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训练班学员的毕业创作一问世,便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至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在欣赏詹建俊的新作时,眼前总还要映出《起家》的影子。那大气势的构图、强烈对比的色彩、宽阔而跳动的笔融、低伏的草丛、翻卷的篷布及大动态的人物在画面上所构成的奔放的韵律,无处不体现出詹建俊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二十多年来更加成熟也愈加丰富了。
在詹建俊的早期作品中,人们自然还会记起《狼牙山五壮士》。这幅纪念碑式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成功,除了它英雄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构思之外,还得力于大刀阔斧的绘画语言与主题相吻合、相协调所产生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起家》和《狼牙山五壮士》(1959 年)代表了詹建俊整个青年时期的创作风貌。
人们不难发现,詹建俊近年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在他独特的、统一的风格中,又呈现出更为多种多样的艺术风貌。有些作品力图发挥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语言的表现力,或画得很薄,颜料被稀释得流淌而下;或画得很厚,用画刀一层层地抹在画布上。有些在近乎平涂的色块之间,寻求画面情感的平稳;有些则在强烈的光感气氛中,创造了嘹亮的音乐化境界;有些痛快淋漓,与中国水墨画异曲同工;有些却在滞重的笔触中,使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坚实厚重的特点达到某种极致……
詹建俊这种对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语言的表现力的寻求,早在他的学生时代就露出端倪。他从不跟在老师的技法和风格后面亦步亦趋,而十分注意从当时条件下所能见到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和印刷品中广泛汲取营养。在“马克西莫夫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训练班”里,他又是一个“画得不像老师”的学生。
上世纪60 年代初,他的一些习作在院内展出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报纸上还在赫然地“讨论”着印象画派是进步还是倒退以及是否可以借鉴等问题,而他竟敢如此“不写实”不注重素描的特点,如此“印象”追求色彩与笔触的韵味,真是有些“大逆不道”!如此这般,也就难怪后来“文化革命”中,他的那些习作被送进“黑画展”,遭到“批判”了。他本人也曾被说成是“三名、三高”。对此,詹建俊是这样辩驳的:“我除了个儿高以外,别的都不高。”
来结束了那个“假、大、空”、“红、光、亮”的时代,人们对绘画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要求全面解释和恢复艺术的功能,要求它给人们带来美感的享受。詹建俊也激情迸发,又重新开始了探索与追求。他到祖国各地写生,创作了《回望》(1980 年)、《高原的歌》(1979 年)、《帕米尔冰山》(1981 年)、《石林》组画(1978 年)等一大批作品。1981 年他出访西非,又画了一批西非印象的画。这些作品,反映了詹建俊在新时期社会变革当中,对艺术本质和绘画语言特别是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语言,以及对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发展道路等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他经过二十多年的进步和挫折、成功和失败的历程之后,自己艺术境界的升华和向新高度攀登的标尺。
詹建俊的作品不是哲理的,而是抒情的。但是,他却不是“花间派”的,而是“豪放派”的。他的作品具有多种多样的面貌,“豪放”则是贯穿于他全部作品中的一条主线,是他的“个人风格”。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从他与中国画的“血缘关系”中得来的。
1948 年他考入北平艺专之前,一直自学中国画,不知“素描”为何物,只是为了考试,经人点拨,才画了两张石膏画。1953 年中央美术学院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系本科毕业,又由组织分配到“彩墨画系”(即中国画系)当了两年研究生,向蒋兆和先生学习水墨人物写生,随叶浅予先生去敦煌临摹古代壁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就悄悄地融注在画家的血液之中了,他在技巧、手段上不断寻求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语言的表现力,正是以在精神气质上、艺术思维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前提的。如果说他1978 年创作的《石林》组画是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追求水墨效果的尝试的话,那么《海风》(1977 年)、《鹰之乡》(1979 年)、《清风》(1983 年)和《潮》(1984 年)中“风云流动”的骨架线则是着意于中国画式的“气势”和“韵律”的结果。
近几年来,詹建俊经常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他在上面画了许多一两厘米见方的构图,颇有些像中国的篆刻图章。他在一幅画的创作思维和酝酿中,总是反复经营推敲这样的小构图,而一般不再作放大稿。他说:“画小反而能见出大;画好小,方能经营大。”他认为,画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大的“势”、大的安排、大的骨架、大的节奏和大的对比。他在这些小构图的反复经营过程中,已经把握住了画面所需要的最根本的东西,而在画布上落笔时,则更注意作画状态和即兴发挥。这似乎也是“大写意”画法,不是冷静地对着模特儿找关系,而是处于一种“神遇”的心理状态之中。在笔与纸、笔与画布接触的一刹那,画面、工具、手、眼、心的回路接通了电流,感情的闸门已经打开,心灵深处的情思奔涌、倾泻在画面上。
来诚然,这种画法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基本功,没有经过写生而“烂熟于心”的形象储备,是不能奏效的。而这对于一个青年时代受过八年正规绘画训练的詹建俊当然问题不大。同时,没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没有将各门艺术融会贯通的悟性,也是不能达到这种境界的。詹建俊既喜欢贝多芬、肖邦,也喜欢斯特拉文斯基、格什温;既喜欢京剧、评弹,也喜欢单弦、京韵大鼓;既喜欢达芬奇、安格尔,也喜欢毕加索和非洲雕刻。他正是在这种广博的艺术学习中滋养了自己。
詹建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在美术学院学习,毕业后留在美术学院工作,再无其他“惊心动魄”的经历了。然而,他也并未游离于社会实践之外,从未脱离生活、脱离时代与人民。他始终以自己的作品和作品中的思想、风格,映照了自己、映照了别人、映照了时代、映照了社会。
艺术,毕竟是感情的轨迹,心灵的轨迹,人类生命的轨迹。“不光用眼、用手去作画,而且用心灵作画。”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詹建俊传授给学生们的心得之言,确是道出了自己在艺术上所不懈追求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