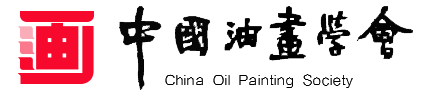吕品田
| 现任: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 《美术观察》主编 | |
| 博士生导师 | |
| 全文化宣传系统第三批“四个一批”人才国 |
复兴手工劳动的一种人文理由 手工劳动所发展的技术形式,是“我的延伸”。(图1) 在手工劳动中,“在我”之手和它所依属的生命本体,劳动者的整个身心,即时即地、身体力行地构成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劳动时空即为生命时空。手工具等技术形式在人的身体外端延伸了“手在我”的本体性质,并因为这种本体性质,它延伸了作为“这一个”的“我”。这种意义的延伸维护着包含在一身之中的那些难以穷尽的身心属性,具有对“我”而言的直接真实性和完整性。然而,在工具等技术形式的现代发展过程中,“我的延伸”已经被另一种延伸??“人的延伸”所中断。这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 “延伸”,是现代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与人的生物学构造是相互联系的。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技术哲学。1877年,德国学者E?卡普在《技术哲学的基本观点》中,以人类学分析为基础,通过把人体解剖学和技术发明的比较,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认为工具以至整个技术客体本质上是人类躯体的延伸,或者说器官投射、器官外化。譬如,砍砸石器和铁榔头延伸了拳头,弓弩和钳子延伸了手臂,衣服和房屋延伸了皮肤和毛发。“延伸说”通过自然角度的审视,揭示了人造物的人类学基础和本质,把整个工具或技术客体的发展,整体地归入“人的延伸”过程,从而也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把握工具或整个技术本质的思想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从手工具到日趋自动化的现代工具,被视为人性或人类躯体延伸、投射或外化的形式,具有性质的同一性和意义的连续性。这一延伸过程也被加以进化论的理解,以为技术的推进和技术客体的演变形式是人类生物进化的延续。人们相信,从手工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工具日益进步和完善,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体现着人的能力的提高,昭示着从局部到整体、从器官到神经、从体能到智能的人的持续的延伸或外化。譬如现代电子媒介,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看来,它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与之相比,其它媒介尤其是机械媒介不过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i]专家相信开发计算机的模拟运算功能可以形成人工智能,而它的本质被认为是人脑或人类智慧的延伸。(图2)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现实中,已经越来越看不到它承沿手工劳动的性质同一性和意义连续性。人类劳动方式的历史延伸的纽带,已随现代技术对延伸方向的另行开辟而被扭断。新的延伸方向在强调人与世界对立、割裂物我关系的立场上,从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角度对人及人的功能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把握。即如“延伸说”所提示的物我关系,是在人的生命活动之外的“理性”立场上所“认识”的对象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被视为独立、外在于“我”的客观对象,是可以测量、剖析的纯粹的物体;人的活生生的存在性,其生命功能,其活动内容和行为特征,其作用功效以及所关联的生活意义,被解析为定量式的生化物理指数。总之,通过对人的“理性”分析、化简和归纳,自然科学用数学的平均值构造了一个“人的整体”抽象的人。如胡塞尔所言,这是“对自然的数学化”,它“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ii](图3、图4、图5、图6) 现代技术便是在此前提下,以“人的整体”为“本体”发展现代生产技术形式,进行“人的延伸”的。对现实中的人来说,这种技术形式的延伸可以脱离生命本体,却能以其活动机制产生比依附生命本体更大的功效。无疑,它突破了“手在我” 的生存本体性质,取代了“我的延伸”。手工劳动技术形式所延伸的“整体的人”??活生生的“我”,对它来说不复存在! “人的延伸”体现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取向:高尚的人类生活不是在劳动中展开的,人生境界也不在于体验因生命有所承担而实现的生活意义;人应该征服自然,征服一切物质包括生命物质,俘获它们,让它们为人的“需要”和“生活之累”去作无限的承担,而人应该像上帝那样悠闲而富裕地活着。为此,人必须使自己的全部生命“功能”,从手到脚,从肌肉到神经,从五官到大脑,从记忆到思维,投射到人身之外的物质形式上,实现彻底外在化的延伸。这一切在现代技术理性看来是可能的,因为人的全部生命“功能”都可以用科学技术方法来解析,以之为机械功能、物理功能、化学功能、生物功能等等。人是什么?人是机器! 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因为即使唯有人才能分享自然的法则,难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机器么?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距离成比例地再靠近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就产生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成?[iii]
“人的延伸”被导向机器形式,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当代思想认识,当然不像拉?梅特里时代那么“机械化”。“生物正取代物理,成为社会的主要观念。”[iv]把人看作“机器”肯定比不得把人看作“生物”,但是,人一旦和“机器”结了缘,就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了。 我们不应该试图根据机器来解释人,而是应该反过来:以人为根据来解释机器,以便探寻不断精化机器、改善机器,并把它纳入旨在达到和人的情境真正协调的任务之中的种种可能性。因此,机器可以在一个无限的过程中被“结合化”,也就是被纳入人的文化和历史之的发展中。 从功能的观点来说,如果我们是依据一个生物种类的那些改造环境的生命功能来界定该生物种类的,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样地从生物学上,依据人的功能来界定人。因为根据生物学观点,毕竟是技术使得征服环境,从而使得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技术构成了人的进化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未完结的过程;而且在技术今后的发展中,人可以说将不断地把深藏在其表层之下的新的潜能外在化。[v] 这是皮尔森写在《文化战略》书中的一些话。引用在此,不仅想提示有关延伸理论的当下认识,还因为这位学者强调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很能反映西方学界的前沿思考。如中国学者闵家胤在该书中文版前言所说:“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科学的理解。因为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出新的信息概念,在各个领域揭示出信息的存在和作用,并且还有力地论证了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鉴于这一点,不妨把皮氏的想法稍作展开。在他看来,人和自然的关系始终是非常紧张的,人必须以“文化战略”反抗自然,赢得自己的生存、自由和发展;文化发展“并不总是在进步”的三阶段模式,各有其积极和消极的倾向,我们应扬长避短地“找到一种文化战略”,“根据一种图式或模式将文化问题工具化并能解决它”。[vi]他把解决问题的思考总括为“我们对社会、工作、家庭方面的技术所采取的态度。这种技术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扩展,甚至是我们大脑的扩展(信息技术)。我们加强了对这个世界的掌握;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人组织能力的作用(包括它的强弱)问题,变成了加于这种能力之上以迫使其做出审慎决定的压力问题。”他强调,在延伸人类的现代技术已有力掌握世界的情况下,应该加强人自身的能力和伦理道德以更好地运用现代技术,继续人类的“解放的历史”。不同于以技术发展解决技术发展问题的方略,这种努力向自身去求的方略,很能代表当代西方学界的“人文化”倾向,其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很显然,他的方略透露了西方学者对现代技术的沁心入骨的信念,坚信其本质是“人的延伸”。因此,恐难指望其“文化战略”会引发崭新“态度”。尽管反现代化思潮在西方很有声势,却难以从现代技术的影响及其滋生环境中完全摆脱出来,他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未免还是“技术的态度”。所以,皮氏对现代技术“延伸”人的方式及其前景,充满乐观: 正因为人用他的工具延伸了他的身体,所以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活动范围:他能够用工具来补充软弱的身体器官;能够用工具来观察和测量(空间和时间);能够让工具工作而他自己休息,用机器或设备监控而他自己睡觉;但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如此地变革、替代和改进工具,以致用这种方式对他身体的延伸看来很可能会永远地发展下去。[vii] 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人的这种方式的“延伸”,持续地把手和人的“内部性”物我关系外在化。现代生产方式不再立足“手在我”的生存本体基础,将身心一体、物我合一关系视为“缠手”、“缠身”、“缠心”,作为人类的负担而彻底甩手。现代技术以“理性”所外化的“抽象的人”或“人的整体”为原型,将其延伸为机器化的“手”。高科技的“机械手”,为之作了形象的诠释。这抽象化的“手”,以重复的机械动作外化了人手的抓握功能,的确身手不凡、功效极高,只是与手的抓握动作紧密关联的生命内涵和人文意义荡然无存!整个现代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如同一只巨大的“机械手”,不歇手,不撂手,也不信手、失手;它满天下转手、倒手,满世界伸手、下手,可谓一手遮天的强手、硬手和快手。这只“手”以越延越广、越伸越远的“间距”与人离异。倘若依然把现代技术哲学所强调的“人的延伸”作为人类工具或技术客体发展的内在经络的话,那么,这个从来被视为现代技术伟大成就的“间距”,却根本地离间了现代工具与手工具、现代劳动与手工劳动的性质同一性和意义连续性。(图7) 作为“人的整体”的延伸,现代生产方式以它的技术形式开发世界空间。巨大的工程、巨大的厂房和巨大的城市,像一头头怪物,吼叫着从天地之间挣脱出来。它们被赋予一种绝对的空间品质,不再受运动、变化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所局限,成为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开工生产的普适空间。它们“间之”于天地,不再承担和维护天地万物充满生机的空间展开。空间的局限性被克服了。现代技术还征服了时间,这是更具决定性的一面。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按技术理性的原则和需要重新分配和使用。现代能量形式予钢铁机器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并内在地具有一种绝对的时间性质,可以摆脱自然的生命运动规律,不知“疲倦”地连续工作。“休息”作为劳动承担性的体现及其人文意义,被现代生产方式所否弃。技术理性的世界需要不落的太阳,现代技术的“电光”将世界白昼化??所有的“不可见”都大白于天下。整个生活的世界,无论从时间意义上还是从空间意义上,都被现代生产力一一打探过了,以致原先关于它的一应美学观都随“客观现实”的真相大白而变得“无理”。[viii](图8) 现代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割裂了空间和时间在人的劳动过程中的自然统一,消除了各自的局限性,确立了“虚拟”与“复制”的生产运作机制。“虚拟性”和“复制性”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基本特性,具有极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效益中心原则的体现。 可以在劳动实现性意义上认识的虚拟性,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化处理”,即通过“分割”时间来取得恒定的空间形式。可以在劳动持续性意义上认识的复制性,意味着空间的“时间化处理”,即通过“重复”空间来造成循环的时间形式。杰恩?米利拍摄的《毕加索》(图9),用现代摄影技术为我们形象地描述了“虚拟”与“复制”的生产运作机制,并直观地展现了空间和时间统一体被分裂的“过程”。手划过黑暗空间的过程被小手电光切割为一个个“亮点”,虚拟出一个亮线构成的“现实空间”??半人半马像(时间的“空间化处理”);以长时间曝光技术一点点“复制”在胶片平面上的瞬间空间现象,集合成“时光”的流转运动(空间的“时间化处理”);整个画面体现了一个分裂的“时?空”结构:图像?人物场景(最后瞬间的闪光灯造型)和时光?“光画”(之前动态记录)。在现代生产方式中,这种分裂的“时?空”结构,排除了时间绵延和空间变化所造成的复杂性,免除了对付和处理这种复杂性的经济学负担。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被作为一种具体的制造活动而预先以数学方式加以描述和设定,所有的东西都在理性规划中被明确化,所有的偶然因素都被这种理性的逻辑所排除。针对具体制造目标而展开的“劳动”,形成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循环运动体系,“生产力”的运行情况尽在预先的掌握之中。这一切确保了资本投入的一次性和准确性。随着这个封闭体系的循环运转,资本便一劳永逸地开始其一本万利的增殖过程。这就是“批量生产效率”的哲学透视。 脱出生存本体的功能关系的外在化,消除生命蕴涵的功能的工具化,使得物我关系出现巨大的裂痕。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物”和“我”各自都被赋予一种绝对的空间品质而空间化,彼此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绝对空间意义上的关系。生态世界的时间性质??物的活性和人的生命性,[ix]不再以空间的流动性、变化性和复杂性为存在,转而以可人为遣调、支配的无形能量为表现。原先基于“手在我” 的生命化的 “物”和“我”,蜕变为物理化的“时间化的空间”(运转的机器)和“空间化的时间”(人工的操作),相应的时空一体关系也蜕变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现代技术进一步把生命时间(人的智能、气力;自然的地气、地力)作为“元素”,从原先的载体(身体或生态自然)中“抽取”出来,转换成契合机器运转性质的“时间化的空间”(工作规程、各式应用软件等;电、核能或太阳能等)。于是,生态的世界和这世界中的生态事物,都被加以“空间化”处理,都被消除了原本体现生命时间的变化性、复杂性和偶然性,而呈现为单纯的“几何式的”存在??“‘纯粹’体,‘纯粹’直线、‘纯粹’平面、‘纯粹’圆形,和发生在‘纯粹’圆形中的运动及其规定性。”对此,胡塞尔说“凡是在几何的空间中观念化地‘存在’的东西都是在其一切规定性中被清楚地预先决定的东西。”[x]这样,世界的一切,包括人自身和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都可以通过数学方式来作统一的理性把握和处理。如今,发达的信息处理技术,便是如此地把一切对象都转化为“空间性”的“比特”[xi]??一种现代算筹,变得可以运算了。这就是所谓的“数字化”。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数字化”就是“几何空间化”,“数字化生存”就是“几何空间化生存”。人们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图像化时代”或“读图时代”,是对这个时代的“本质”或“时代精神”(包括审美精神)的一种直观,透辟之极! “数字化”或“几何空间化”,为现代物质生产带来极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也把虚拟化和复制化的影响扩展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图10)有关这两方面问题的考察和分析,拟结合手工劳动特性的论述来进行。在此,只想简单化地作个提示,即:“数字化”或“几何空间化”的本质是反人性的、非生命时间性质的。推演其结果,终究是生态世界的毁灭,是人类的毁灭!这未必是危言耸听,因为,科学家们已经在考虑以“非躯体智慧”进行太空殖民了。[xii]之所以要“非躯体”,是因为躯体是生存本体的,具有生命时间性质,它无法耐住漫长的星际旅行;之所以取“智慧”,一方面因为它被认为是“人的本质”;一方面则因为它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数字化”为比特。比特是抽象无形的“计量单位”,不占体积,没有重量,可以“打包”、“压缩”,既节省“空间”又无“时间”限制。所以,让 生命形态化为“比特”,漫游星际广宇??摆脱地球上的劳动生活以至彻底休闲,恐怕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最终归宿。(图11、图12)
无奈“躯体智慧”遏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实不知摆脱地球劳累的“非躯体智慧”,究竟会是怎样一种“快活”。疑惧之下,我们不如直面劳累在地球上的快活,手工劳动。 [i] 参阅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ii]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27页,第71页,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iii] 拉?梅特里《人是机器》第52页,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iv]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72页,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v] 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第132页,第122页,第137页,刘利圭、蒋国田、李维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vi] 同上,第3页。闵家胤在中文版前言中归纳道:“关于文化战略的变迁,这本书给出了一种新的三阶段的简化模式。这三个阶段是:(1)神话的(或原始的)阶段;(2)本体论的(或科学和技术的)阶段:(3)功能的(或系统?信息的??这在书中没有明确地说出来)阶段。……在神话阶段人同宇宙是统一的……在本体论阶段人同周围世界拉开了距离……到功能阶段人消融在发挥功能的关系网络中了(这一点在书中也没有讲得很明确)。”
[vii] 同上,第123页。
[viii]笔者因参与编撰一个主题为“艺术与科学”的专题电视片,亲闻一位颇有资历的电视编导这样批评古人的月亮审美观:他们太无知,太缺乏科学思想,所以编造“嫦娥奔月”,其实月亮上只有环形山和它的影子,而古人却以为是玉兔金乌什么的。
[ix] 20世纪20年代,创立生物圈学说的苏联科学家В.И.维尔纳茨基提出“活物质”的科学概念。他把参与地球化学过程的有机体的总和称为活物质,认为:组成这个总和的有机体只是活物质的一些部分,活物质中不仅必须包括有机体,而且必须包括它周围的与它有联系的死物质、外部环境;一种“我们至今还不了解的‘生命’本身,调节着经过有机体物质的‘生命旋涡’”,改变了物质,使外部环境参加有机体的整个化学反应,决定并引起有机体成分的变化;“这种活物质和死物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符合自古以来的观察和人民的经验。”参阅В.И.维尔纳茨基《活物质》,余谋昌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x]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29?30页,第26页,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xi] 比特(bit),即二进制数字(binary digit)英文缩写的音译,是二进制信息量的计量单位,由贝尔实验室的J?W?图契最初使用。像电子一样,比特没有体积,也没有重量,可以传播文字、图形、影像和声音,并通过多媒体方式传播综合信息。
[xii] 参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书中的《无躯体能否思维》一文,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节选自博士学位论文《动手有功??手工劳动人文特性和意义的当代审视》第二章,标题为节选所加。发表于《必要的张力》(设计大讲堂从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