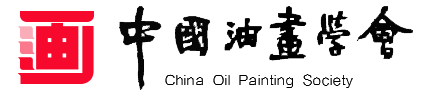吕品田
| 现任: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 《美术观察》主编 | |
| 博士生导师 | |
| 全文化宣传系统第三批“四个一批”人才国 |
眼下,街心广场、户外雕塑、景观装置、园艺造景之类的公共艺术形态如雨后春笋般蔚然而起,给城市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不管其中是否夹杂着名不副实的东西,公共艺术日益升温的现象终归反映了中国城市建设不断走向深化的趋势。如今,开路架屋的“基建”已成规模,关乎现代城市社会整合的文化“装修”却有待投入。作为文化建设实践方式的公共艺术,正准备接受召唤的使命。 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艺术,它有“公共”之限。在现代汉语中,“公共”一词含义明确,只有一个义项,即“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按词义,字面上的“公共艺术”即当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艺术,性质有别于挂在私人家里的艺术品。 然而,社会实践中的公共艺术,却不像字面上这么简单。在现代文明和现代城市条件下,要使公共艺术高度公共化,真正具有为社会所共有共享的公共性,就要直面那繁多而又必须解决的实践课题,譬如,需要维护地方以至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综合利益,需要尊重反映地缘历史与现实状况的风土人情,需要适合城市既定或规划的空间秩序和功能,需要遵循艺术自身的美学规律、技术要求和评价标准,需要建立包括决策与民意交流互动、创作主体资格认定和权限规范、常规程序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在内的整套运作机制,等等。抛开这些不谈,我们首先要直面的是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认识问题:何为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这是正确把握公共艺术的认识前提和基础。
从根本上说,公共艺术公共性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精神实质或价值取向的一元性。这种一元性体现了政治学上的权力概念,可以将之理解为既定的有组织的权力结构以非强制性权力形式对个体实施有意和有效的影响,以达到有益全社会的预期目标。从社会学或文化学角度来看,这种一元性是社会控制和文化渗透的体现,即社会规范通过一定形式影响个人行为,使个体在接受这些规范的内在化过程中趋向社会化。“文以载道”、“寓教于乐”则是美学对这种一元性的表述,它意味着可令大众喜闻乐见的多样化形态始终体现着整合社会的道义。以“公共”面目出场的艺术未必是公共艺术,但公共艺术一定是公共性的。对于这种公共性,也许应该这样表述:诉诸美学形式的意义呈现明确的实践指向,体现着政治权力、社会控制、文化渗透和审美教化所追求的统一性。时间维度上的公共性是流变的,有着历史的规定性;然而,空间维度上的公共性则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维护伦理规范、塑造社会人格、培养善良心性、增进文化认同、弘扬民族精神的必要条件。公共艺术公共性的生成,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实践,它需要排除“多元化”的干扰。 目前,对于公共艺术公共性的把握还存在着认识误区。其中“开放说”影响最大。这种认识专重空间形态,强调公共性体现在公共艺术依存于开敞的公共场所,以致公众皆可凭身体或视觉与之直接接触。应该说,这种空间开放性确是公共艺术公共性的一种形态特征。这使得一些在法律上属于私有的艺术形态,如私营商场、私营社区的公用艺术设施,可能会实际地具有公共性;然而,也不能就此认为,那些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艺术形态就一定会缺乏公共性,如国家或市政重要机构、军营、校园里的公立艺术设施。显然,空间开放性不是把握公共艺术公共性的绝对依据,但是开放说”却难免带来一定的迷惑,以致我们的政治权力、社会控制和文化渗透会变得“盲视”,浑然不觉各色“私念”在光天化日下取 “公共性”而代之。一些或戏弄公众智力或放纵“身体”、“视觉”欲望的伪公共艺术,其“合法化”理由竟如此简单,空间大敞。 “开放说”纵容伪公共艺术,却障蔽了把握公共性的深邃眼光。倘若我们参透公共艺术的“一元性”,就会意识到公共性既可以诉诸公众身体或视觉的直接接触,也可以诉诸其他途径的间接接触(如通过报刊电视,在此意义上,一个城市或社区的公共艺术不独属于这个城市或社区,其公共性意义已超越了地缘限制),甚至还可以通过“封闭”方式得到体现(如古代衙署的“正大光明”匾额即通过对官员内在心态的影响来产生及于广大百姓的公共性效应,而百姓却无缘直接接触)。开放的空间形态可寄公共性,封闭的空间形态同样可寄寓公共性,因为公共性的实质不在于艺术的空间形式,而在于其精神蕴涵的一元性。是故,公共艺术应该有甚至覆盖广告、纪念币等形态的广阔外延(鉴于此,目前对公共艺术所作的形态学认定是否合理,甚至于作这样的认定是否必要,仍值得商榷),而无比丰富的公共艺术又在精神实质上超越地缘空间、超越法律领属地而直属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公共性给予公共艺术以穿越时空的感召力,长城,长城考察站升起的五星红旗,流光溢彩的元宵龙灯……它们寓寄并透出的精神存在,把地处边陲、侨居异邦的民众也拥入了自己的空间怀抱。实际上,公共艺术能否成为大众的“共享空间”,并不取决于人的身体是否可以或者是否被允许与之接近,关键在于蕴涵其间的精神是否能在心灵深处唤起一种人文归属感。 除“开放说”外,还有从创造主体方面来考虑的“下放说”。这也是有普遍性的一个认识误区。这种认识依照“后现代”主张阐释公共艺术,认为应该“去中心”,将空间营造权“下放”到个体,以致把个体的“参与性”视为公共性。这种主张看似充满民主色彩,开的却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没有哪个老百姓参与了实际创作,也没有哪一种方式集中了民意(有人说得对,任何一种对民意的集中方式实际上已经“非民意化”了)。但是,这种主张倒是给了艺术家以自我表现或恣意妄为的机会,也给了决策者以懈怠职守或假公济私的方便,大家都可假借“民意”巧夺或亵渎营造权,结果,私语喧哗,乱七八糟。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总和权力紧密关联,是社会资源的集约,根本体现着一种社会化的权力意志。张扬权力民主,与拒绝一切权力一样,都会摧毁公共性,这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幻想。其实,踏上“去中心”的歧路,再谈公共艺术就是巨大的自我嘲讽。缘“个人主义”的逻辑起点前行,西方意识形态势必陷入无限“延异”的困境。德里达、利奥塔等一批“后现代”冷面学者,已无情地宣告了西方启蒙理性的死亡。可怜的哈贝马斯满怀责任感,在破碎的公共领域殚精竭虑,试图重建“交往理性”,这实在是一种崇高的荒唐。在这个世界上,资本主义无孔不入,它用资本控制了社会权力意志,以致像德国这样一个重“理性”的国家,竟然能为“广告效益”而容忍克里斯多夫对公共领域实施“私欲强暴”,包裹国会大厦。 我们为什么如此恐惧权力,以至于在最不该拒绝权力的领域拒绝权力,提倡“个人主义”的“自由性”?问题恐怕在于我们失落了一种政治智慧。其实,整合社会的权力可以不取“强制”和“外力”形式,而内化为个体的自觉需要,表现为大众对“天地良心”等公共性的深心认同。这当然是仁学的伟大贡献和儒家政治的巨大成功。受仁学儒政教化的中国民众,旷日持久地从事着公共艺术的创造,他们总在祠堂、戏台、庙会广场和灯会的夜空下演绎时空一体的宏大公共艺术,一代又一代地以民居戏文雕刻化育高尚的道德情怀。在这里,权力和艺术达到了最高的和谐,公共性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由此想到对于“慎独”的个体,“外力”打造的“公共艺术”恐怕是多余的。应该说,在大众自发创造且彼此沟通的意义上,这种融合公共性的民间艺术体现了权力的民主化,显示了最积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自由色彩。反观时下一些或碍于长官意志、或为了资本扩张、或任由艺术家自以为是而制造出的“公共艺术”,除了搁置在公共场所外,又哪里谈得到什么利于社会整合、人格培养和精神塑造的公共性?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问题不是空间支配权该由谁来掌握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管理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该怎样支配自己的公共空间,该往这个空间灌注怎样的东西的问题。在中华文明史上,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始终密切交流,不像欧洲那样彼此对立。从一个极端越到另一个极端、颠覆空间支配权的“公共艺术革命”,在中国既没有文明基础也没有文化理由,中国的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从来共同遵循仁学主导的人生哲学,并把这种哲学灌注到整个公共空间。 出于防范艺术家“专权”的考虑,一些认真的艺术家开始提倡“放弃”,譬如《深圳人的一天里》的策划者喊出了“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的口号。创作中,“雕塑家被告知,千万不要试图表现什么,或者体现什么,不要手法、风格、个性,雕塑家的任务就是原样地复制对象,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翻制工的位置上”。(孙振华《雕塑空间》)这种抵制艺术家“专权”的诚心的确感人,任由市民“灌注”的虚心实在可敬。但若真是如此,恐怕“公共性”也就成了公共垃圾桶一般的“实用性”,是人都能把“一孔之见”投入这空空荡荡的“桶”中。 难道公共艺术的使命和归宿真是在于这种“放弃”之中吗?
发表于《美术观察》2004年第11期;《雕塑家通讯》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