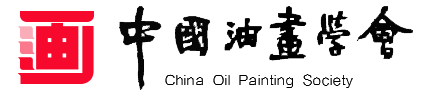吕品田
| 现任: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 《美术观察》主编 | |
| 博士生导师 | |
| 全文化宣传系统第三批“四个一批”人才国 |
热带非洲艺术的价值重估
在人类文明史上,非洲大陆热带区域的文明形态始终被人类认识的“黑色”所笼罩。时至今日,“黑非洲”这一概念的修辞成分中,仍隐隐夹杂着蒙昧、野蛮、落后、悲惨、邪恶和虚无等消极的认识成见。即便历史上曾有诺克、伊费和贝宁等辉煌的艺术创造,“黑色”的成见仍使得非洲艺术,被整体地“黑”入艺术史的原始艺术范畴。 对非洲艺术来说,它所隶属的原始艺术范畴,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时间长度”和相应“时间价值”的特殊范畴。这在文化人类学上的对应含义是“未开化”。因此,在关于人类艺术发展的现成话语阐释中,非洲艺术“以其无有历史为特点”(热尔曼?巴赞:《艺术史》)而仅有一种“空间价值”。欧洲现代艺术家??他们通常被看作是真正发现非洲艺术的功臣??所认识、所接受的,大体也就是这种片面的或被扭曲的价值。关于非洲艺术的既有价值定位,无疑体现了文明价值观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主导艺术阐释的西方话语。实际上,非西方文明形态的所有其它艺术传统,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语境中,像非洲艺术那样都免不了被人“黑”一家伙。因此,认识热带非洲艺术的价值,与认识我们的艺术传统一样,具有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意义。 非洲艺术的发现,是属于欧洲人的“专利”,更确切地说,是其掠夺世界、扩张霸权的“副产品”。非洲艺术被发现的历史,乃是非洲民族被征服、被掠夺、被欺凌、被歧视的历史。 自十字军东征以来,非洲引起了欧洲人的好奇与幻想。中世纪满溢眩光异彩的海外奇谈,以及基督徒心中关于“在黑大陆有一个被上帝遗忘了的、崇拜偶像的王国”的神话,不妨视作欧洲人于15世纪开始其深入内陆的“探险”活动的体面诱因。但是,“事实上,远在黑奴贸易兴起以前,经济需要已成为欧洲人探险的主要动力之一。”(让?洛德《黑非洲艺术》)当时欧洲货币交换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金本位制的恢复,使欧洲人对黄金倍加渴望,并把贪婪的眼光投向非洲大陆。从此开始直至20世纪上半叶的掠夺行为,使大量非洲艺术品远别“黄金海岸”、“象牙海岸”,不断入充到欧洲的私人奇物室、国家博物馆、旧货市场以至艺术画廊。 早先,欧洲人打量非洲艺术品的眼光,完全是蔑视性的。一般人仅止于猎奇心的满足,而最早作研究工作的文化人类学家,也只是想从中了解土着民族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这些知识对欧洲人的殖民事业是必要的。至于对待非洲艺术本身,人们的认识和态度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以为它是处于文明进化低级水平的蒙昧艺术形态。直到今天,这种认识和态度也很难说有根本的改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砥毁和破坏后,20世纪的现代艺术运动,最终启发了欧洲人对非洲艺术的欣赏。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和德国表现主义者等一批现代艺术家,不仅高度评价非洲艺术,而且从中汲取变革西方传统艺术的创作灵感和形式因素。以至于“原始主义”作为对未开化民族“原始艺术”的“原始性”的崇尚和追求,成为贯穿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级现实主义的一种相似艺术倾向,甚至还不同程度地影响或渗透其它现代主义艺术。尽管原始主义者对原始艺术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但他们共同强调和接受的所谓“原始性”就在于这种艺术形态所具有的从内到外的“单纯性”。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非洲艺术不仅以分明的轮廓、简扼的塑造和稳定的程式显示了艺术形式的纯粹性。而且以这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将一切偶然的因素强有力地统一到内在感情,一种被认为属于人类本性并体现其原始或基本性质的审美冲动,的直接表达上。对原始主义者来说,如此意义的非洲艺术显然比欧洲古典艺术更接近艺术的原始性质,更吻合他们在现代文明的异化现实中维护自我价值的心理需要和追寻个体生命意义的审美旨趣。后一方面乃是欧洲现代艺术家发现并重估非洲艺术的真正立场和实际角度。 从人类目前的生存状态来考虑,现代艺术家由非洲艺术中发现的“单纯性”,不只是对西方世界,也对业已卷入现代文明潮流的非西方世界,都切实地构成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价值。面对现代文明所导致的普遍异化或分裂,所谓非洲艺术的“单纯性”为现代人提示出一种审美解救方式,一种诉求个体生命体验的逸出线性时间的空间化方式。这种方式的把握已经成为现代艺术的革命性成就,它表现为以纯粹的艺术形式和直接的审美体验,超越被线性时间所统治的有限现实,使相对于“我”的一切外部的、现实的、历史的“物”,皆在主体心境中与人的自由理想交融统一。基于这种方式的审美经验,同时返身作用于现代人,使之倍觉单纯性的非洲艺术有?种返朴归真、物我化?的现代感。 不难理喻,“单纯性”作为对非洲艺术的一种肯定性价值看待,如同早先众口一词的鄙视和否定,完全是欧洲人从自身利益和自身遭遇来考虑问题的产物,其价值内涵根本得之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投注和规定,其现实意义也根本取决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追求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美学角度的肯定性价值看待,是以“未开化”、“无历史”等文化人类学的否定性价值看待为前提的。如同其物质形态被从母土中拽出来,沦落为漂泊异邦的民族志标本或猎奇者的收藏,非洲艺术的精神形态也被从所属的社会文化机体肢解而下,成为漫游异质文明环境的一种异化的抽象概念形态或失落“时间意义”的纯粹“空间价值”。显然,无论褒贬毁誉,对非洲人民所创造并真正属他们的艺术来说,既有的西方话语都不可能构成终级的价值判断。 不要轻信东非大裂谷是人类发源地一类的科学神话,那是生物进化论预设的陷阱。绕到社会进化论那里,你便会看到人祖是怎样忘恩负义地撇下终究“未开化”的一支给黑非洲,而带着高智商的主力落户欧洲大陆,并从此随时间的直线推移向人类的高度文明一路挺进。出于对西方话语的警惕,我们宁可相信时间像个圈是循环往复的。?种文明就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就是?种文化。它的价值和它的发展程度,并不以非其文明非其文化的外在“直尺”为绝对衡量,只能就这种文明这种文化针对一方水土?方人的适应性和适应程度相对而论。任何文明任何文化,一旦脱离既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便成了不可同日而语、等量齐观的他物或死物。 因此,有必要对非洲艺术再作?种价值判断。 倘若不蔽于成见,何尝不可见得这一点:非洲艺术自以不可磨灭的文化特性和美学特征,提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话语却与非洲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的“艺术”概念。像许多非西方艺术实践皆有体现的那样,这种“艺术”概念并不以可以独立看待和单纯把握的艺术性为艺术的本位价值,它强调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全面融入、全面承诺或全面体现,承担社会生活所期望、所需要、所赋予的又非其不能的价值担待。与其说这样的艺术不存在本位价值,不如说它的本位价值所执不以西方话语的艺术性,而以本土话语的“艺术性”为据。 就活跃并作用于本土社会生活的非洲艺术而言,其“艺术性”体现在一种样式、一种造型、一种纹饰或一种颜色切实地实现了它的某种或某些价值担待。失去这一定的价值担待,或者所担待的不是社会化的价值,那么,作为艺术形式的上述任何成分,其本身则不足以自立自为,无从可言“艺术性”。因此,以社会价值担待为本的非洲艺术,总是和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信仰以及伦理道德等广泛的社会实践混合交融,并作为载体或媒介在整合社群、规戒示范、鼓动生产、记述历史、交流思想、传播知识、证明身分、昭示责权、惩罚褒奖、祈禳疗治以及寄情娱乐等复杂的社会功利方面,发挥积极而特殊的作用。大量材料表明,传统非洲艺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某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是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需要,而且这种关联往往以随俗的方式得以实现。多贡木雕中有一种双臂高举的传统雕像样式,依照风俗习惯,多贡人有时把它作为祈雨之物,有时则用以解释如何行动会有利于生产劳动。面具对非洲许多民族都是重要的,用途极其广泛。部族庆典、人生礼仪或祈禳活动中的歌舞当然少不了面具,就是惩罚罪过,酋长也要戴上特定的面具以显示其权威性。显然,原生形态的非洲艺术,是本土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不曾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或价值独立性。一言以蔽,非洲艺术是不具有独立性质也不以独立性质为终级价值追求的艺术,它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单纯性”企图。因此,可以把“混合性”??一种介入并体现社会生活复杂关系的非独立性质,视为非洲艺术契合其民族文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文化特性。 在遭遇西方文明的分裂力量并受其破坏之前,非洲各民族的传统艺术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性。尽管各民族信仰和文化并不统,但如同撒哈拉史前岩画、乍得或尼日利亚的古代陶塑与青铜艺术以及班巴拉人、多贡人、塞努福人、巴加人、巴库巴人、巴卢巴人晚近的木雕艺术所显示的,非洲艺术的“混合性”文化特性经受了巨大时空跨度的考验,而不曾为政治演变、朝代更替或外族入侵所改变。这是文明活力的使然,是民族信仰和文化内在连续性的使然。非洲民族普遍崇尚的祖先信仰和来世观,使他们对沉浸于习俗的艺术始终保持深信不疑的价值认同。在非洲艺术那里,混合性的“空间价值”是有“时间长度”有其“历史”的,它不是原始艺术。毫无疑问,在欧洲人闯入之前,黑非洲还没有谁会想到把时间拉直来测量自己是否“进化”。 非洲艺术与其文化特性相对应的美学特性是原始性。不同于欧洲现代艺术家所理解的“原始性”它丧失了“时间”维度而仅剩单纯性的“空间价值”。这种原始性在于艺术的原始状态和性质未因文明的历史推进而瓦解或异化。现代人为之殚精竭虑的弥合有限与无限对立的问题,在“未开化”的非洲人那里是不存在的。保持生活和价值混合性的艺术形态,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消除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自由与必然、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个体与集体、审美与实用对立性的通道或架构。或者说,非洲民族自持的信仰和文化,根本没有也不能把困扰欧洲人的一系列思维性质的对立范畴引入他们的宇宙和人生。对他们来说,天地万物是个生命统一体,普遍的灵性在其中往来穿行、自由流淌。通过一定的方式,人们可以和它对话、交往,使之顺随人意。艺术时空即是灵性通达、人事化解的证明或预示。在非洲有一种旨在让年轻人学会遵守社会规范的授奥仪式。仪式中,授奥者要戴着面具代表神灵施教;结束仪式时,全村人要参加集会,“在戴着面具的舞蹈中,奥秘的意义被召唤出来:以往的少年死去为的是在新的环境下作为成年人而新生。”(让?洛德:《黑非洲艺术》)现住在尼日利亚中部地区的部族,像早先创造诺克艺术的部族一样崇拜祖先。他们认为祖先像是生命力的源泉,生者可以从中接受到这种力量。基于灵性所维护的统一世界,艺术没有理由要从中“升华”出来,做所谓“纯审美”的孤家寡人。在非洲社会生活中,艺术是可以诉说一切的语言、沟通一切的途径、体现一切的载体,它被那里的人民视为与普遍灵性打交道的适当方式。 原始性,赋予非洲艺术以特征明显的感性魅力。基于视觉接触的审美体验,我们可以用激情奔涌的热烈、如鼓如舞的律动、恣肆率性的强悍、天真自然的朴拙、神秘莫测的深邃和酣畅明快的显达,来描述包括绘画(岩画、壁画等)、雕塑(陶塑、铜像、木雕、牙雕等)、面具、编结、织物、服饰、化妆、环境布置以及匠心独运的实用造型和装饰图案在内的整个非洲艺术的感性魅力。我们还可以透过因复杂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以及复杂历史和社会环境而格外纷繁的艺术现象,归纳非洲艺术普遍呈现的一般特征,即结构表意化、造型程式化和形象情境化。 非洲艺术的结构,像欧洲艺术一样表现为视觉形式元素的结构,但不取决于形式趣味和形式法则。它强调并体现“意义”的联结,以“意义”本身的圆满构成为原则。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意义”与纯粹个人旨趣无缘,其根本来源是以传统风俗信仰为载体的历史性集体意识或社会意识。?种表现妇女捣舂黍米的多贡小雕像。其“意义”在于奥贡王的生命和黍米的增加有对应关系。当地流行的一个神话故事,确立了这种“意义”。对于这类雕像这样的内在结构,视觉形式元素本身,诸如其性状如何、关系如何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紧要的是它们必须顺应圆满构成一种“意义”的中心需要。我们由非洲艺术形式所感受到的,那种不论具象或抽象、平面或立体、软材或硬质而一应的夸张、变形和概括,都是结构表意化的自然形式效应。 缘自历史性集体意识或社会意识的“意义”,通常具有高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通约性。“意义”的这些特征,必然会反映到艺术处理上并通过相应的艺术处理不断加强。造型程式化便是由相应的艺术处理体现出来的一种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的价值,并不在于一种程式便于作者驾轻就熟地处理艺术素材,而在于它有利于广大的社会成员轻而易举、准确无误地识别和领悟艺术中的“意义”。即如刚才提到的多贡小雕像,有关人物个性的素材对它毫无价值,但“捣舂黍米”作为,种造型姿态的程式,却于关联神话阐释的“意义”有利害关系。对非洲艺术来说,这种艺术特征不能仅从艺术风格学上理解,而特别需要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把握。它是非洲艺术针对“意义”的圆满表达和传递所呈现的一种静态形式特征。 几乎所有保持艺术原始性的艺术,都是“动态”的。非洲艺术更是如此。对于生活在传统风俗信仰中的非洲人民,艺术中的“意义”不是仅供思考仅作审美的,它是参与并影响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具有切实的人文功利价值。因此,艺术必须进入社会生活,并只有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意义”的价值和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形象情境化便是非洲艺术针对“意义”的真正实现而呈现的一种动态形式特征。这意味着非洲艺术是不能从它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割裂出来的,而它的真正价值意义,也只有生活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非洲人民能够真正地、深切地领悟。 这套书系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视觉接触非洲艺术的机会。出于对这一机会的重视,通常不列入非洲艺术(热带或黑非洲艺术)范畴的埃及艺术,在本系中被特地安排了一定篇幅。保持非洲地理概念的完整性是?种考虑。更主要的是,还考虑到埃及艺术虽有文化上的特殊,但地缘关系使之与腹地的黑非洲艺术不乏古往今来的联系,尤其是在民间。同样出于对这一机会的重视,重庆出版社的涂国洪先生以他学者的智慧和诗人的热情,还有显而易见的辛劳,为本书系图片资料的遴选、编排和说明,提出了很多中肯意见,谨此深表谢意。非洲艺术一直末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的介绍和研究工作更是凤毛鳞角。限于条件和水平,书系中难免不足和讹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原载《非洲艺术》书系,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
《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0年6月21日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