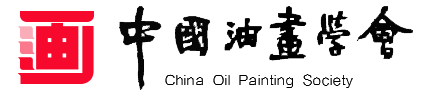吕品田
| 现任: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 《美术观察》主编 | |
| 博士生导师 | |
| 全文化宣传系统第三批“四个一批”人才国 |
中国民间文化观念影响下的审美情感态度 生活,在庶民百姓的心目中,不单是追求物质、满足物欲的日常营生,还是一种观照人生、寄托情怀的介质。朴素的世俗生活以它载负、实证人生意义的时空存在,无边而随机地激发和唤起人们丰富的情感体验。人们会在流动的每一种生活形质上,发见精神的光辉和生命的色彩;人们也会赋予生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以神圣的意味和亲切的情趣。庶民百姓对待生活的创造性的审美情怀,让朴素的生活显示出人文的美丽和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意义。百姓对于民间生活就像植物对于土地那样依赖和贴近,那样熟悉和热爱,而中国百姓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深深地结缘于伟大的土地。一种缘自土地的朴素而自然的天质弥散于中国民间特别是乡间日常生活之中,也一直透入那些凡夫俗子的生命机体而在他们的心灵里扎根和升华。稻谷收获后,人们不会忘记首先给司掌、照料土地的社?和先祖献上清香四溢的新米新面,让他们和自己一块享受丰收的喜悦;亲人远游他乡时,家人总会塞上用红纸裹着的一包灶土,让他带去乡土的庇护和安身立命的土壤;人们知道在某个时节、用某种形式给兽虫、牲畜、花草、树木等等大自然的伙伴庆贺生日,而且他们乐意在自己过年时也给小猪、槐树、石磨或马车披红挂彩……所有这些行为举止都强烈地表露了中国老百姓那种带有“土地”之天质的情感,显示了中国老百姓热爱现实生活的鲜明情感态度。 众所周知,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与人的需要之间的某种关系的反映,即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心理反应。它表现为主体对待客体的一定的主观态度,这种态度与人的利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只有那些与人的活动、需要、要求以至理想有关的对象,才能引起人的情感反应。虽然情感并不是审美心理活动所独有的,但它对于审美创造以至审美欣赏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且审美活动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伴随着鲜明的情感态度和强烈的情感体验。审美情感主要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不是宣泄物质情欲的生理快感。因此审美中的情感活动,有别于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活动。然而,因为情感态度密切关联着人与对象的利害关系,关联着人的需要和理想,现实中的审美情感便会因人的不同利害、不同需要和理想而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中国老百姓的审美情感与日常生活情感往往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事实上,对庶民百姓来说,那些合目的性对象的感性形式所唤起的愉悦生活情感体验与审美情感体验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对他们来说,“美”和“善”几乎同义,“善的”也就是“美的”。如果认为这种倾向不过是一种准审美情感态度的表现而予以轻视的话,那显然是一种美学的偏见。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百姓往往以审美情感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他们往往能主动地从现实生活的感性形式中体悟出“美”、生发出“美的”感受来。或者说,他们总能把生活本身的内容和形式能动地理解或改造为“美的”,以至更能够创造性地从中获得一种审美精神的愉悦,使得平常的生活充满非凡的意义,使得自己不至于在不尽如人意的现实面前沮丧、消沉、颓废或堕落。常闻一种或许有点夸张的说法:“老百姓个个都是艺术家!”。若以现代认可的艺术家职业标准来衡量,此说自然难以成立,但论日常的审美敏感和把握现实的审美态度,老百姓却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在发现生活的审美价值方面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审美地对待生活以至由看似平常的事物寻求审美体验方面有着独到的能力。我们实在不该藐视这等事件的深刻意义??一位不得不出门劳动的普通母亲,为了让孩子安全地“抛锚”在炕上,会想到用红布带子一头拴着孩子一头拴着石狮子。这平凡的生活事件在母亲的处理下顿时充满审美意味,可以设想到,一个缺乏审美敏感和审美情趣的人是万万不会这样处理事情的,她很可能只是像拴小毛驴一般把孩子拴在一块普通的石头上。 还可以列举大量衣、食、住、行方面的实例来说明老百姓对待生活的审美情感态度。民间生活中许许多多用文字难以表述的审美现象,是每一位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可能从中看到的。这里,我们着意要阐述的是:一种鲜明的审美情感态度何以普遍地在民间百姓那里表现出来,而且这种审美情感态度总是使主体将审美创造旨趣融会于现实生活需要的主题。 这种原因当然很容易被看作是现实生活实践及其特定要求。在总体上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也的确可以构成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的笼统性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沦为教条的复述,以致漏失一个存在于智能和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事实上,它以理性和情感因素的历史累积,构成一种超时空地影响主体审美心理能力的酵母。我们所指的是民间文化观念,因为它能够跨越时空地传播,使庶民百姓集结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下,这面旗帜的口号是:能动地感受和创造生活!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民间文化观念对老百姓审美情感态度的影响。 就反映人自身的现实需要和理想的内涵方面来说,民间文化观念可谓纯粹的“心上之音”,它的本质特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表露。这种性质的文化观念,一开始就把主体的注意力和感受力引向了本己之心,敦促主体真诚地倾听心灵的呼唤、尊重心性的要求。 受特定文化观念的指引,民间百姓根本地立足在一种全面占有世界的要求和理想基础上来对待世界。因此,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摆脱心灵的主观性,单在世界物质实在性的单一向度上建立心理表象和理性知识,或者单为人际社会规定性的制约而泯灭生命之情。他们总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去感知世界,对客观事物进行评价和选择,并竭力按照自己的要求、意愿和理想,根据自己的兴趣、好尚和习惯去从事某种活动。他们虽然没有高深的学理,但自明“本于心”的那根“尺棒”和那棵“随心草”,即如我们常常能从老百姓那里听到的说法:“做耍货没有一定的尺棒,手就是尺棒,眼就是尺棒,想着怎样好看就怎样做”;“泥货是随心草”。[1] 这朴素的自明便是深刻学理的直觉体悟,它所显示的智慧与《庄子》所言“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和“任其性命之情”的自觉学理如出一辙。古代一些真正能够站在“情”的立场上思考的哲人,显然比迂腐的理学家们来得清醒明智,他们从实现“政治”的意义上,肯定了庶民百姓“求之于情”,“至情”而后“至性”的智慧和态度。袁宏道曾谓:“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以民之情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从理上去,必至内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为害也,不知理在情内,而欲拂情以为理,故去治弥远。”[2] 作为社会化的主体意识系统,民间文化观念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已深深地内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成为人们行为活动的内在指针。庶民百姓因此不至于内欺己心、外拂人情,而能秉“情”之矩尺丈量世界、权衡人生、营度生活。他们直率地说:“我的笔是随心走的,稀奇百怪、五颜六色……画画为了好看,总要选‘趣’的画。”这话表达了他们对待艺术创作的主观态度,也表明他们对生活的审美表现总是和从情感、情趣上来把握现实对象的情感活动紧密联系。文化观念造就的目的意识和认知模式,使老百姓习惯于从本己的心性要求和美好理想出发,将认识对象和自我的现实关系转化为情感关系。正是这种原因,他们会觉得把鸡脚板画得像朵花比画得真像鸡脚板“好看”“有趣”;会认为它“不比真的像,但是比真的好看得多”;会感到“画画的时候,自己心情也很愉快,有时一画画自己会笑出来,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3]在民间,激发艺术创造冲动与兴趣的情感态度和情感体验朴素而热烈,它是推动民间审美创造活动普遍、持久开展的强大而直接的心理力量。 人们之所以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去感知世界,满怀炽热的情感去创造艺术形象,也与民间文化观念提供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关。 原始先民感知世界、从事造型活动的强烈情感态度,关联着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原始人在一种幻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混同交织的心理状态中,不自觉地也必然地会把自然的东西弄成一种心情的东西,这种感知心理状态本身就伴随着一定的情绪或情感。随着人的错觉、幻象或梦想在表象思维过程中被类比、比附为世界表象,或者被外推、投射为世界现象,生命一体化的原始世界观由此产生。这种世界观还不能自然地理解生命的朴素意义或世俗意义,其视野中的生命表象是一个个奇异怪诡、魔法无穷的神灵鬼怪,它们以超验的力量占据着世界空间并点化了万物的神圣性。充满这些表象的原始人的心理世界,经常处于复杂的情绪或情感状态,他们自然常用一种“心情”的眼光对待世界、对待生活。 民间文化观念所包含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最初源出于原始的世界观。在漫长的流变过程中,文明因素的增进虽然不断地削弱着其中的蒙昧成分,但是原始世界观所造成的影响并未彻底消失。那些奇异诡秘、虚幻绚丽的原始表象或者保留在神话、传说以及民俗习惯中,或者保留在人们朦胧依稀的潜意识的记忆中。总之,它们仍借文化观念的传承机制或多或少地残存于民间社会意识系统。不管多么微弱,这些残留的星火??它们曾经是照亮洪荒时代的熊熊烈火??仍然可以点亮情感的油灯,带给世间一个昏黄而暖意融融的氛围。倘若肯定《山海经》《聊斋志异》的神奇文字意象曾经激活过一代代人的幻想和情感世界的话,那么,可以设想那些被认为就生活在人们周围的原始鬼怪神?的激发力量是何等的强大。今天,仍有农村大娘在乐滋滋地剪着她们的“鱼精”、“蛤蟆精”或“妖精飞人”。史俊英大娘说:“飞人胖娃,娃是蛤蟆精、鱼儿精。它想变蛤蟆,又想变鱼,两手在头上举灯高照,下面是坐莲,古时人有翅膀。”[4] 当她们在生活世界中寻找“精”时,当她们在艺术世界里塑造“精”时,那种心理情感波动的强度能够等同于一般的审美情感体验吗? 诚然,神妖鬼怪之“精”毕竟是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当工业技术缩小了世界空间之后,就像环境污染不容得那些可爱的自然成员??动物或植物??一般,缺乏灵性的思想也不断地驱赶着那些本不应该被人讨厌的“精”。不过,生长“精”的土壤,并不是靠围海造田、开山征地的力量一下就能改造完全的,至少可以说这是中国广大乡村的情形。所说的这种“土壤”指的并不是那种带有保护性的物质空间,而主要是具有再生之力的精神空间。这种精神空间最初也是原始先民用生命一体化的世界观塑造的。很难说它会像它的创造者那样成为历史,或许,它还会成为原始人对于当下以至未来人类文明的永恒惠赐??它的文化意义已见诸文化哲学的思考。 如果说,生命一体化的世界观可以在哲学家那里表述为生命本体论的话,那么,这种世界认识在老百姓那里却以最朴素、最实在、最明快的情感态度表现出来。哲学家的理解会表现为“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念,而老百姓的看法则会表现为给小猪系红头绳或者用红纸裹一方灶土这类温情的俗常行为。不言而喻,一张红纸,一根红头绳,所裹系的不只是某个小东西,而是整个世界和人生;所裹系的不仅是某种物质,而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和深刻的情感。在我们看来,其意义和价值不亚于庄子或海德格尔的沉思。中国老百姓的朴素信念,可沿“天人合一”哲学观的思想逻辑来推演:既然人的生命和养料归于天地的覆载化育,那么,同出于这种覆载化育的宇宙万物,亦如人的生命那样是有血有肉、有灵有情的;那么,在天地之间展开的生命万物的运动过程及其具体细节,亦如人的生命运动过程那样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种信念缘自情感体验,体现着人的情感态度。中国老百姓便是用这种情感态度对待世界,用这种情感拥抱世俗生活的。天地人间的一切,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生活与审美,悄然无声地沟通于这种情感状态。这种状态何尝不是审美的? 民间文化观念提供给庶民百姓的人生观,是务实的、乐观的、趋善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性质,是为始终以维持、发展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为思虑焦点和价值核心的有机需要观念所决定的。本着他们的需要观念,中国老百姓把对敬爱、尊重、理解、贤智、审美以及自我能力实现等等所谓高级需要的追求,统统叠合在对求生、趋利、避害基本需要的卑近凡俗的追求活动中。他们的人生满足感,他们的人生幸福感以至他们的自我实现感,都是从日常生活的温馨感、富足感和如意感中发散升华出来的。在老百姓看来,人丁兴旺、壮健高寿、家邻和睦、五谷丰登、囤积富裕、风调雨顺、居行常安等等都在是人生的美事,委实是“吉”,是“福”,是“喜”,是“如意”。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若能在这些方面显示出能力,就有可能得到众人和社会的敬慕和褒扬。人们亦以这些美好事物为目标,相互鼓舞,相互竞力,相互敬让,相互祝贺。 在这种人生观和需要观念的影响和促动下,人们满怀生活的热情,以各种方式来追求需要的满足。民间美术创造活动便是人们在不尽人意的现实遭遇面前,用以保持乐观刚健之心态而采取的一种替代性满足需要的方式。它们的主题大都围绕着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而且,它们大都是为着满足自我或亲朋好友的精神需要。因此,从自我切身需要出发,围绕现实生活主题,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基础而非冷漠的交换基础上展开的民间美术创作活动,自始至终地伴随着炽热而真挚的情感。从事民间美术创作主要是寄托自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展示自我对人生未来的理想,表现自我切实的需要意向。艺术主题与生活主题、审美意识内涵与功利意识内涵的统一,使老百姓能够在造型活动中集聚生活的热情、汇合生活的情趣,从而形成甚于专业艺术家的主观情感态度,产生甚于一般艺术创作活动的强烈情感体验。 此外,从民间文化观念的结构特性来说,反映民间社会成员内心意愿的求生、趋利、避害观念本身就含有浓烈的情感因素。这些观念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逻辑概念形式的思想,而是情感化了的思想,它们包含着主体从内在要求出发去认识外部世界所不可避免的感情色彩。这些观念之所以能在民间构成一种导向艺术实践、激发和支配人的创造行为的积极力量,正在于它们是一种理在情中、情理交融的情感化了的思想。因此,在民间美术创作中,观念的表现也就是情感的表现。 正因为老百姓的审美情感是与日常生活的情感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混同统一的;正因为老百姓对待造型活动的情感态度是高度主观的,伴随的情感活动是热烈奔放的,所以民间美术才总是充满浓厚感情色彩、富有强烈生命节奏和生命流动感的。强烈的情感冲动状态,使他们不拘囿于形式规范和经营法度去作刻意的雕琢,而往往是大刀阔斧、恣肆纵横、一气呵成。这种创作状态造成民间美术形式结构的天成之趣,具有刚健质朴、粗犷豪放、简约明快、浑厚自然、热烈绚丽、亲切温润的感性品质。 在民间美术创作活动中,想象和情感活动活跃地交织并交互作用。情感是激发想象的力量,它使想象增添了浪漫的色彩;想象亦激发着情感,它使情感体验更为强烈和深刻。而促成这两种心理活动活跃地交互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是民间文化观念。
注释
[1] 转引自叶又新《山东民间玩具二题》,载《美术》1982年第10期。所谓“耍货”、“泥货”,是为儿童制作的玩具。
[2] 袁宏道《德山麈谈》。
[3] 转引自曹金英《金山农民画家谈创作》,载《美术》1982年第8期。
[4] 转引自靳之林《抓髻娃娃》,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