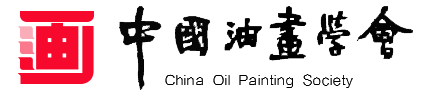吕品田
| 现任: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 《美术观察》主编 | |
| 博士生导师 | |
| 全文化宣传系统第三批“四个一批”人才国 |
文化自觉与二十一世纪亚洲艺术发展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亚洲的辽阔大地上,不息地流淌着的大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恒河、印度河、湄公河以及长江和黄河,就像一条条巨大的乳腺,在自己的流域里哺育了美述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等伟大的历史文明;滋养了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道教以及儒学等影响深远的伟大宗教、哲学和思想体系。源自不同民族的人文创造,带着赋名为“亚洲”的土地的色彩,在比照于所谓“西方”的巨大“东方”时空中,汇成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的亚洲本土文化。丰富多彩的亚洲艺术便为这丰厚的本土文化传统所激发。 审视历史,无论价值内涵还是物化形态,古代亚洲艺术形态具有充分体现各民族文化精神取向和发展规律的自律性,同时也具有深刻反映地缘关系中文化交流所造就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可以在一个客观而又广阔,一个不含价值判断或者价值歧视的认识视野,借助其它地缘文化的关联性得到一种相对的体认。譬如,比照于欧洲文化所表现的抗拒自然、强调人的个体性并依靠“思维理性”来把握世界的倾向,亚洲各民族文化则倾向于顺应自然,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体认宇宙法则的“实践智慧”。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大体折射了欧洲与亚洲的文化精神,喻示了各自艺术追求的价值核心。对亚洲文化来说,除了普遍的生命秩序和法则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立的事物,也不存在彼此间的绝对界限。任何生命价值及形态的实现,最有决定性的就是顺应“神的意志”或应合宇宙生命运动的统一法则。因此,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都被理解为体现某种决定性力量的普遍生命运动。也因此,从人的观念到人的行为,包括艺术活动,融入宇宙的生命运动都是一个根本而永恒的母题。造型艺术往往被欧洲人视作纯粹的精神形态。但在亚洲人这里,它是与其世界观紧密关联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期望融入宇宙生命整体的一种生命化媒介。在一定环境中,在某种条件下,它甚至被看作生命形态或生命形态的延伸。尽管渊源不一、流行错综、种族繁多、信仰纷杂,尽管媒介独特、手段各别、风格多样、趣味各异,造就了亚洲艺术显而易见的个别性,然而,诸如非投影法的平面性、散点性构造、非视觉真实的自然状态追求、非影调与色彩关系的线性造型处理,还有随处洋溢着的既刚健又温厚的生命活力,依然是提示其整体性存在的普遍表征。由这些表征,可以感受到基于地缘关系的亚洲文化价值核心的存在和作用。事实上,文化传播借助历史的地缘关系强化了亚洲艺术的整体性,譬如印度的佛教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化等都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对包括艺术在内的亚洲文化形态和品格产生过超越原发区域的广泛影响。这种大范围的文化传播,伴随介入当地民族文化传统的本土化过程,造就了一个超越民族或政治疆域的庞大艺术帝国。在基于地缘关系而历史地形成的“亚洲文化圈”中,亚洲人从容自信、自得其乐地从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信念出发,用自己的传统艺术方式去表现自己所理解的世界,去揭示自己所尊崇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切合本土社会需要和人文理念的亚洲艺术,也在长期的历史中切实地维护着亚洲世界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并因此成为推动亚洲文明发展与繁荣的生机勃勃的重要软力量。 亚洲的文化精神以及显示在艺术形态方面的整体性因素,在习惯于分别对待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人文与自然、现世与来世、真理与经验等关系的欧洲人看来,具有“非理性主义”或“神秘主义”的性质和色彩。出于欧洲文化立场的这种解读,由于不可能从生活其中的生存经验中获得深切的认同感,以致必然地成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性质的话语。这种误读或臆想性质的话语,在殖民主义的现实政治意图和攻城略地的霸业中被有意地加以利用和强化,并化作所谓的“东方学”而成为一种谋略隐伏的文化工具或机制。即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书中所揭露的,“作为一种文化工具,东方学中到处充满着强力、活动、评判、真理愿望和知识。东方是为西方而存在的,或至少无以计数的东方学家是这么认为的,这些东方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要么是家长式的强加于其上,要么是肆无忌惮的凌驾于其上……”实际上,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语境或话语霸权中,亚洲艺术以及非西方文化形态的所有其他艺术传统,都不免要被“东方学”加以“东方化”甚至“妖魔化”,以至于非西方文化的所有这些文化表现形态,都不再是他自己,而只是西方的附属物,是用于比照“文明的西方”和“野蛮的东方”的永远的“他者”。 当然,排除殖民主义的现实政治意图,出于特定文化立场或特定生存经验的误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这也构成文化交流和影响反而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原因。所以,文化误读本身并不一定就是破坏力量,真正的破坏力量是在这样一种关系情境中构成的,即:一当某种文化误读为所误读的对象自己所接受、所认同并奉之为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时。正是因为隐伏着霸权主义的现实政治意图,“东方学”便总是努力让世界人民以为它所追求的是普遍真理,或者它所揭示就是普遍真理。
对于亚洲来说,不幸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西方霸权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亚洲国家纷纷落败。亚洲人包括大多数亚洲学者,都把这种失败视为自身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失败,而把导致现实失败的殖民主义历史运动及其文化体系视为现代化。由此,“西方中心主义”就以“现代性”的面目赢得了亚洲的认同,成为贯彻到亚洲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的“世界主义” 或“普遍真理”。 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政治意图,借助亚洲世界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文化摧毁而达到比军事力量更深更广的程度。近代以来,亚洲文化演进的格局和取向深受西方世界的影响,以至于亚洲的现代化包括文化的现代化过程皆以学习和模仿西方为目标。在亚洲发展观中,出于不同语境、诉诸不同形式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价值取向,曾经寄托着亚洲人的深切希望。然而,伴随这“希望之旅”的,却是亚洲文化。维护亚洲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软力量”的不断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发达的全球信息网络带给他们的文化传播优势,一方面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输入非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一方面竭力垄断和操纵国际舆论,利用文化手段巩固其强权地位,维护其全球利益,以至追求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战略目的。在西方的文化渗透中,像热带雨林遭遇疯狂砍伐一般,亚洲国家的文化格局遭到空前破坏,文化传统受到严重威胁;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不仅通过市场占领严重影响亚洲国家的文化产业,更使其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归结为“西方文化的全球化”这一切,最终会对亚洲民族的文化生存构成毁灭性打击。 就亚洲艺术的现代形态而言,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多已被西化。现在所谓的“现代化”、“现代性”都是西方话语业已界定的东西,支持、激发亚洲人表达自身审美阐释和审美情感的“文化立场” 渐趋丧失。这种情形在亚洲艺术领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实,在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台北双年展、光州双年展、釜山双年展、横滨三年展、福冈亚洲三年展等大规模展览上,我们所看到的亚洲现代艺术形态绝多是一味“与国际接轨”的。我们的艺术家在为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艺术成就而眉飞色舞、自鸣得意,全然忘却了自己的可悲处境。我们不惜毁弃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背井离乡,在思想和文化上行乞于西方世界,用艺术上的所谓文化反思、政治批判或社会问题关注,为对方端出鉴照亚洲文化“落后”与“愚昧”的镜子。如今,亚洲艺术的现代形态被欧美艺术的阴影深重地笼罩着。 对亚洲来说,二十一世纪充满机遇。这其中最大的机遇在于,今天已有凝重的历史经验、深切的现实体验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来支持亚洲人提出面对未来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诉求。这种发展诉求将会促进亚洲意识的形成,从思想认识上真正消除“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学”的话语迷惑。在今天亚洲的国家关系中,尽管一时难以从地缘政治或地缘文化意义上提炼出一个关于亚洲意识的纯粹概念,但是,近年来亚洲国家日益增强的诉求于大陆本土的文化归属感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全球化情境中,“亚洲崛起”与“回归亚洲”正在构筑着一个体现丰富地缘关系和历史底蕴的坐标系,它预示着二十一世纪亚洲文化发展的一种总体趋势或基本状态。与这种总体趋势或基本状态相适应的建构亚洲意识的过程,将伴随亚洲各国以切实体现民族文化价值的艺术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艺术家进行政治对话、思想对话和话语交换的过程;也将伴随亚洲各国艺术家之间以关注共同文化问题的艺术创作,密切合作、广泛交流、认真探讨,以寻求文化方面的共同利益和核心价值、维护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过程。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通过艺术方式来交换有关亚洲意识的认识,以及在艺术领域所取得的关于亚洲意识的认识成果,将会产生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也有助于亚洲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获得日益增进的文化共同性基础。在实践层面运作的亚洲意识,根本地取决于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文化自觉,对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自我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尊重、遵循和发扬。 展望二十一世纪,“和而不同”的亚洲艺术将成为推动亚洲文化发展的“软力量”, 而亚洲艺术“求同存异”的文化自觉也将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亚洲意识。 发表于2008年8月28日《中国文化报》美术周刊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