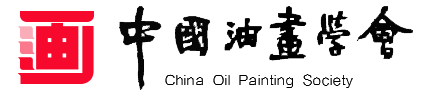水天中
| 现任: | 艺术评论家 |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
|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 |
|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常务理事 | |
|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
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艺术家中,关良是一个按照他自己的趣味活着的人。不但是在艺术上,他的日常生活和心境也是如此。从40年代开始,关良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圈中引人注目的艺术家,但他的大量作品是在50年代以后产生的。在50至70年代间,他是很少的几个没有将自己的心灵和艺术融合于主流意识形态大潮之中的艺术家之一。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明朗恬和的心态。同时代的另外一些艺术家,为了保持自己原有的艺术信念,不得不进入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 关良是广东番禺人,幼时在广州私塾读书,他父亲非常疼爱他,常常带他四出游玩。他骑在父亲肩上,到很远的戏院去看戏,是他最难忘的童年记忆。11岁的时候,举家迁到到江苏南京,住在“两广会馆”紧靠戏台的屋子里,这给了他看戏的方便条件,就此一步步养成了他的“戏瘾”。 1917年,关良到日本留学,对艺术的爱使他改变了报考化学专业的计划,得到许敦谷的帮助,先后到东京川端绘画研究所和太平洋美术学校,在藤岛武二、中村不折等老师的指导下学画。在接收基本写实素描训练的同时,逐渐倾心于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艺术,马奈、莫奈、德加、雷诺阿和塞尚、马蒂斯的作品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凡高和高更的作品更成为他敬仰和学习的榜样。从那时开始,关良已经暗下追求艺术“活”的本能的决心,“艺术要超出静止的美,艺术要耐人寻味”。 在日本的那几年里,除了绘画以外,关良下功夫最多的事是学习小提琴,他拜师学琴,从最基本的练习曲开始,逐渐醉心于古典音乐,一代小提琴大师海菲兹、埃尔曼、克莱斯勒的演奏,使他对小提琴艺术有了很深地领悟。从专业小提琴演奏家的标准来要求,他学琴已经太晚,但作为一种艺术爱好,他所付出的精力和达到的修养在中国美术家中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1922年,关良学成回国。他和许敦谷一起,在上海神州女学教素描课。后来又在上海美专兼授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和素描。并与许敦谷、陈抱一、周勤豪等组成“东方艺术研究会”。许敦谷的哥哥许地山是当时颇为活跃的作家,经他介绍,关良结识了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许多文学家,后来又与郭沫若成为挚友,与“创造社”的倪贻德、叶灵凤、郁达夫、成仿吾……时相过从,并为《创造》杂志作插图和封面设计。和这些文学家的交游扩展了关良的眼界胸襟,对他后来艺术面貌的形成不无关系。而郭沫若对关良绘画的关注与理解,一直保持到他们先后离世。 二十年代在上海的几年中,另一个重要机缘是有幸结识了画家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刘海粟,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点化”关良,使关良进入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高远天地。那几年里,上海举行各种中国画展览,出版历代名贤画册,都是关良研习传统绘画的机会。水墨画成为关良在素描、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之外的又一方辛勤耕耘的园地。 1926年,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胡根天担任新建的广州市美术学校校长,他邀请关良、许敦谷南下,到广州美术学校任教。同年,郭沫若也由上海到广州,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科主任,郭沫若便邀请关良在中山大学附中兼任美术课。 1926年的广州,是全中国革命力量聚集的地方,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国国民党于五月间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议案,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向北方军阀展开全面进攻。富于革命热情的郭沫若成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官员,他鼓动关良也参加北伐军做宣传工作。于是经邓演达批准,关良穿上了军装,成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领导着三十多个擅长文艺和新闻宣传的青年奔赴前线,在硝烟战火中以宣传画、标语参与打倒军阀的激烈战斗。从广州一直到武汉,关良带领的文艺战士从未落伍。从性格气质上看,关良属于传统文化中所谓“逍遥散淡”一路,参加北伐战争,成为一员战士,对他确实是难以想象的生活经历,但他通过了长途征战、疾病、炮火的考验。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的那一天,在硝烟弥漫的武昌城头,在欢庆胜利的欢呼声中,关良想起岳飞《满江红》中的诗句:“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北伐军旅生活成为他艺术体验的一个方面,这在他那个时代的美术家中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南方北伐中原而取得胜利的战事。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发动“清党”,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北伐军中的左翼知识分子离开军队,郭沫若往日本避难。关良先到广州,再往上海。刘海粟欢迎他回来,再次请他到上海美专西画系任教。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关良的艺术生活出现了变化,他对京剧和水墨画的兴趣超过了对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水彩和素描的兴趣。他成了上海演出京剧的各个戏院的常客,看戏回来就提笔蘸墨,画出一幅幅当晚舞台上的精彩瞬间。清晨起来则练声“吊嗓子”。他请在上海京剧界颇有地位的朋友尧伯麟,介绍结识了许多京剧演员,并由一位京剧名角教戏,自己购置了全套老生戏装和道具。经过一段时间勤学苦练,完全掌握了京剧老生唱、念、做、打的基本表演技巧,成为一个很像样的票友。而他对小提琴的感情,这时也移向京胡,由于有演奏小提琴的基础,他的京胡演奏水平提高很快,剧团的专业琴师也常为关良高超的琴艺叫好。20年代末以后将近十年中,关良在上海既教课,画画,又看戏,练嗓子,唱戏,拉二胡……他对这种悠闲而又“繁忙”的生活乐此不疲,直到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这种富于传统文化情趣的生活节奏被炮火打断。 南京沦陷以后,日本兵进入上海,傅雷从内地来信,建议关良去国立艺专教书。他离开上海租界逃往香港。滞留香港期间,在许地山帮助下举办画展,以卖画所得作旅费,经越南河内到昆明。1939年到国立艺专,与滕固、潘天寿、常书鸿、陈之佛、吕凤子共事,后与庞薰琴、李有行等人到成都技艺专科学校任教。三、四年间辗转迁徙于云南、四川一带。 1942年,关良想到西北去。这年秋天,为筹措旅行经费,他在成都举办个展。文学界的友人郭沫若、老舍、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热情为他撰写评论、在画面题诗,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使这次展览顺利举行,40多幅作品售出。关良携卖画钱游览蜀中名胜,然后北上陕西,经宝鸡、天水到兰州。他原来的计划是要沿河西走廊到敦煌去看莫高窟,到兰州以后,才知到从兰州到敦煌这一段路还很长,他单身前往是太艰难了。战时的兰州,文化活动甚多,他在兰州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游览附近名胜,便改变计划,往东到西安,上华山,然后折回四川。这次川陕甘之行,他画了许多水彩写生,后来又将其中一些改画为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在西北高原的山川城郭间,关良亲身体验了汉唐诗人所吟诵的壮阔崇高的境界,这使他的文化胸襟更为开阔。 返回四川以后,应潘天寿邀请,关良于1943年再次到国立艺专西画系任教。这时艺专已经迁到重庆磐溪,日本空军时常轰炸重庆,但在轰炸间隙,艺专师生依然弦歌不息,作为西画系教学主力的关良,也成为学校京剧爱好者的骨干人物,他们的聚会演唱,成为校内外文化生活的盛事。当时远在沙坪坝的丰子恺先生,在他们演出的时候,也要过江来助兴。当年看过关良扮演《捉放曹》中陈宫、《游龙戏风》中皇帝的学生回忆,关良演戏相当“专业”,唱腔极有韵味,有言菊朋、余叔岩风致。 1945年1月,在重庆从事现代绘画创作的西画家发起举办“现代绘画联展”,展览的目的是阐发现代绘画观念,打破国内艺坛陈陈相因的局面。这与关良历来的艺术追求相吻合,他欣然参加。参加这次展览的还有林风眠、丁衍庸、方干民、李仲生、郁风、倪贻德、庞薰琴、赵无极等人,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关良随艺专师生回到杭州,住在西湖边的汪庄,继续在西画系任教,并主持画室教学。他与着名京剧演员盖叫天的友谊,始于这个阶段。盖叫天是一个有深厚文化修养的演员,他们两人相见恨晚,谈画说戏,互相启发,互相争论。盖叫天对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喜爱到极点,曾请关良为他画出全本《武松》,打算刻石镶嵌于他预建的墓穴四壁。可惜这些画稿和部分已完成的石刻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毁于红卫兵之手。 1949年以后,关良和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一样,学习政治理论,改造思想,深入基层锻练。关良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与当时苏联式的通俗写实绘画相去太远,虽然他很认真地继续教素描,但让他教课的时间没有维持多久。像早于他离开学校的林风眠一样,关良也由浙江美术学院退回个人的艺术天地,于五十年代中期定居上海。这使他获得更多自主的时间,可以专注于个人的绘画创作。 关良性格温和开朗,在他当年学生心目中,他“随和而不随便”,是一位“作风纯朴,不以人誉而喜,不以人毁而忧,坦然淡泊”的学者。他中年时期远离权力中心,而五十年代成为文艺界领导的许多左翼文学家又多为他的老友。这多种原因使关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度过十来年安宁顺遂的时光。他的水墨戏曲人物画,在经过五十年代初期的短暂冷落之后,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赞扬,一代宗师齐白石更给予盛赞。1956年5月,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举办了关良画展,12月杭州举办了画展;1957年5月,先在北京举行画展,然后各地陆续举办关良画展。1957年,他和李可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派出的艺术家访问东德,在柏林艺术科学院举办画展。德国艺术家和普通观众对关良的作品非常喜欢,喜欢的程度出乎关良意料之外。他在德国参观心仪已久的西方美术名作,画了多幅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风景,莱比锡的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水墨人物画集,这是继齐白石画集之后德国出版的第二位中国艺术家画集。 1960年,上海画院成立,关良成为上海画院的画师。除了定期学习政治,偶而出外参观、写生之外,画院对画家没有太多的干涉。
国内艺术界对关良作品的赞赏,一直延续到1964年。这一年,文艺界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批示,提出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当时关良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批示,但对他作品的展览、介绍突然停止,所有的剧场也都不再上演传统剧目。到1965年前后,政治风声日紧,关良“自觉地”停止了唱戏画画,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完全地沉默。 严酷的政治迫害是从对京剧的批判开始的,关良如惊弓之鸟,手忙脚乱地销毁自己的“罪证”____戏曲人物画。好在那些画是画在宣纸上的,全家人一起动手,把画放在洗衣盆里搓揉成纸浆,再和上煤灰倒进垃圾箱。紧张劳动了好几天,才算将它们打扫得一干二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对知识分子进行的迫害,还是没有放过这位温和纯朴,自毁“罪证”的艺术家。浙江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把他从上海抓到杭州,批判斗争之后关进“牛棚”,勒令在劳动改造中交代问题。 某日,红卫兵押解关良等教师去批斗,路遇他的好友盖叫天被红卫兵装到垃圾车上,头顶扫垃圾的畚箕,在街头游街示众,以示横扫“封资修”文化垃圾之意。盖叫天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后死去。两个被“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揪斗的艺术家在街上低头擦肩而过,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相会。 那时候,造反派抄家、游斗、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必然锣鼓喧天。从小喜欢锣鼓声的关良从此对锣鼓深恶痛绝,用他的话说,“耳闻锣鼓声,胆颤心又惊”。在上海,红卫兵认为他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徒有其名,根本不会画画。把他拉到他家所在的弄堂口,摆上课桌,让他临摹初级中学图画课范本,周围观者如堵。红卫兵要叫关良这个反动权威当众出丑。在忍受各种花样翻新的折磨时,关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毁掉了一切画具,发誓永远不再提笔作画。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极具戏剧性的形式突然收场。人们对意料之外的这一消息欣喜若狂。沉静如关良者,也无法按捺心中的狂喜,从不喝酒关良上街卖来白酒和毛笔,热泪盈眶地举杯。他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提笔作画的一天!
关良的绘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水彩、素描和水墨画。前者题材多样,后者则以戏曲人物为主。虽然外界对关良的艺术印象大都来自他的水墨戏曲人物画,但关良很看重自己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 关良对西方绘画的兴趣,集中在19至20世纪之间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中间。他在日本学画时,在掌握写实技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当年的学生娄世堂回忆,五十年代初期,杭州艺专组织教师下乡,要求每人交一张表现农村新面貌的作品。关良画了村干部开会讲话的速写,回校后让同去的十几个学生给他作模特儿,“关先生写实工底极深,不但把我们的神态画得很像,而且把我们全神贯注听报告的情景表现出来了”。这大概是五十年代以后他唯一的“主题性”创作。平日教课时,关良总是要求学生掌握严谨的造型基础,但他自己所追求的是通过强烈而表现性的笔触和色彩,表现充满活力的人和自然的韵律。高更和凡高的作品给了他许多启发,他注意到他们既是自由和夸张的,又是纯朴和不做作的。这些特点在关良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作品中也得到发扬。 关良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大都画得自由而轻松,不像同时代有些画家常常显得拘谨吃力。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风景画中,关良善于把巨大的空间、复杂的色彩关系和质量结构单纯化,但又善于表现出景物的气势。不论西湖一角、长江万里,像《夜泊》、《三峡》、《猎》等画,都是言简意赅。风景中的人物一般都画得很小、很拙,但神气十足,为景物提神。《嘉陵江》画中激流中的船和拉纤人的身影,使这幅画顿时生气勃勃。五十年代在德国的一批风景画,清新洒脱,似乎异域风光激发了画家的创造活力,画面显得特别轻快明朗。 关良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人物不多,但像《戏曲人物》、《后台》等作,确实是当代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中的精品。他的静物画保存了较多后印象画派的风格,又有中国传统写意绘画的风味。这种风味在早期的插图、水彩中表现得也很明显。 关良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但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关良之前,有王一亭、陈师曾的市井人物画,有吕凤子的水墨人物画,和关良大致同时的丰子恺,更以近似的人物画风格广受瞩目。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怀有温情的幽默,以水墨钩勒为主要表现手法,描绘身历亲闻的人物。对于关良来说,戏曲故事中的古代传说人物并不是他所要描画的对象,他所描画的是他在舞台上见到的角色和场面。戏曲对于关良有着特殊亲近的感情联系,他画演员的表演,也在画他自己对这一场面、这一情节的感受和理解。关良回忆他和盖叫天的一次讨论,盖叫天认为关良画错了一个角色戴帽子的方式,但关良坚持不能照搬舞台人物:“这就是戏和画的区别,你要整齐,我要自然”。 作为画家的关良,与作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等人,对舞台形象的关注点显然不同。关良注重的是包含着情感的特殊形式,而郭沫若等人注重的是舞台形象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以及讽喻指向。这种区别在关良的绘画处理和郭沫若等人给关良作品的题跋上表现得很清楚。从题材的选择看,与其说关良选取舞台形象是为了达到某种教化目的,不如说它是一种非政治化的艺术行为,一种对现实环境的逃避。现代中国的人物画家在绘画题材选择上对戏曲、舞蹈,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特殊偏爱,实际上都含有逃避现实生活方式对人的限制和压抑的动机。这种限制和压抑包括视觉形式方面的限制和压抑。 关良对京剧的爱好和修养不但是他绘画创作的动力之一,也是他绘画创作构思、具体处理的参照系之一。但更加重要的是关良首先是一个有着敏锐形式感而且艺通中西的画家,正如徐虹在论及关良的艺术时所说:“他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是要对长期形成的固定水墨形式进行改造,将民间的趣味和水墨的诗性结合,将舞台表演的丰富形式扩充水墨的表现范围,使水墨表现性有进一步发挥”,“关良留给20世纪中国艺术的遗产是一种天真自由的水墨表现样式。”
参考书籍
《关良回忆录》 关良自述,陆关发整理,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烽火艺程__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黎力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巨匠美术周刊?关良》 徐虹撰文,台北锦绣出版公司出版
《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关良画集》郭沫若编,四川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关良》 台北大未来艺术有限公司编辑出版
《林风眠、关良纸上作品集》陈惠黛编,台北大未来艺术有限公司出版
历史环境与艺术的意义 艺术作品的“意义”,是现代艺术批评理论中的热门话题之一。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是否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各家各派人言人殊。但经过长时期的争论之后,批评家们在这一话题上总算得到了一些相近的看法,那就是艺术作品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观者可能对作品有不同的感受,这使作品具有多重意义。但一件作品确实有着不随批评者主观意志变化而变化的“意义”。目前我们看到的围绕某些绘画、雕塑以及戏剧作品的不同理解和争议,都与艺术批评理论发展中早已争论过的话题有关。 在国内文艺界,对于60至70年代出现的一些艺术作品,如中国画《人民公社食堂》、泥塑《收租院》、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毛主席去安源》以及“样板戏”、浩然的小说等等,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和评价。我觉得这种越来越大的歧异,主要是由于有些批评家在解释作品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作品创作的历史环境。 艺术创作的历史环境,对于解释不同的艺术作品有不同的影响。我们面对潘天寿画的一只老鹰、黄永玉画的四只螃蟹,不了解创作的历史环境,不至于对解释和评价造成很大误差。对于潘天寿画老鹰的历史环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黄永玉的四只螃蟹画于“四人帮”覆灭之际,了解这一点,对作品的解释就会深入一层。而在解释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毕卡索的《格尔尼卡》时,画面上的人物、事件以及作者作画时的历史环境就绝对不可忽略。如果忽略或者不知道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历史,就根本不可能对这一类作品作出正确的解释和恰当的评价。 国外文学理论家曾多次以一首名为《送寄生虫出境》的诗为例,说明了解历史环境对于正确解释和评价作品的意义:
他们就要穿过国境,/这些寄生虫,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将在国外乞求别人的怜悯 ,/ 诉说流放的无辜和不幸 / ……如果我们的好意,你们用拒绝回敬,/ 如果你们收留这群畜牲,/ 那么,你们就是用自己的身体,/ 去哺育这些害人精!……
你将如何解释这首诗? 如果不说明这是纳粹诗人 A.安纳克在30年代希特勒驱赶犹太人出境时创作的作品,一切“美学”、“形式”、“结构”分析都将落空。无独有偶,夏晓虹在《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中(《读书》1999年11期)提到一位日本军官的《渡鸭绿江》:鸭绿江头万里秋,人间为客亦风流;扁舟行载渔郎去,唉乃一声下义州。“若不知写作背景,你会以为这是一位与柳宗元《渔翁》诗中意趣相仿的世外闲人,优游山水间。而真相却是,其所过之处,山河易色,草木皆腥。” 类似的例子是30年代后期德国艺术家创作的以歌颂土地、母亲为主题的绘画和雕塑;二战时期日本画家创作的机翼影子下的中国古老城市的绘画。如果不顾创作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而着重分析其“现实主义因子”与“人性的全称命题”,我们将会得出什么结论?
对一般作品来说,作品的题材不等于作者对题材所涉及问题的态度。但在50至70年代的中国,在体制内的艺术集体中完成的集体创作,绝对不可能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艺术家或者艺术集体创作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艺术作品,就是参与正在进行并已经确定了目标和手段的政治行动。这在他们当时发表的文字中(如《人民公社食堂》画幅上的题诗、《收租院》创作组发表于1965年、1966年的文章、《毛主席去安源》的创作者发表于1966年的文章以及有关报道)都有直截了当地声明,不需要我们再来考证和推测。解释和评价这类作品意义的途径是把作品“放回产生创作冲动思想的源泉中去”(谢尔曼论绘画的背景知识)。对于这些作品,就是把它们放回极左的政治环境中去。
1958年夏天,江苏国画家创作《人民公社食堂》,除了实践领导出题目的中国画集体创作之外,创作的目的是赞颂、推广亿万人民进公社食堂吃饭这一荒唐的决策。历史背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国大办食堂,宣传“吃饭不要钱”的后果,是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集体和个体利益,加剧了“三年暂时困难”。凡是当年吃过食堂、在农村体验过“三年暂时困难”的人,都会记得人民公社食堂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灾难。 与《人民公社食堂》相似,解释《收租院》,就不能不联系到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文艺、教育问题上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倾向。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它在氛围、心理及情感上是对'文革'的一种极其适时的支援”(孙波语)。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之前,这一组泥塑就已经被定性为“文化革命一大胜利”;解释《毛主席去安源》,就不能不联系到党内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和造神运动高潮的出现,不能不联系到作品是肩负“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使命出世,并在那场“路线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冲锋陷阵的历史作用。这才是这些作品的原初意义所在,清醒的读者只能从反讽的角度去品味“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理想化的人间乐园”、“时代的样板”、“中国艺术经典”之类的谵语。至于“后现代”、“波普艺术”、“先锋艺术”云云,只是艺术界时贤的郢书燕说,属于无可无不可的范畴。 当然,对于非记实性艺术作品来说,历史环境的意义不是这样明显和直接。关键在于作品的类型,即作品与社会历史连接的形式和程度。从写意花卉、人体雕塑,到表现风俗、历史的写实绘画,再到描述具体事件和历史过程的纪实性雕塑、绘画,显然不能采取同样的解释、批评方法。I . A . 理查兹在论述语言的文学功能时,将其区分为 意思、感情、语气、目的四个方面。在不同的写作格式中,四个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按他的方式看前面提到的美术作品,可以看到,通俗的写实作品注重的是(艺术)语言的“意思”和“目的”。而表现性、抽象性作品注重的是“感情”和“语气”,即讲话者个人的感情色彩、感情风味和讲话者对于听话者的特殊态度。当艺术评论不加区分地淡化不同类型的作品与历史环境的关系时,实际上是掩饰(艺术)语言的“意思”和“目的”,而片面强调了“感情”和“语气”。从当时《人民日报》、《美术》发表的创作经验看,从头到尾强调既定的“意思”和“目的”而控制个人的“感情”和“语气”。建立“创作组”、核心组之类的集体,而不由艺术家个人负责完成,正是要从组织形式上对此加以控制。泥塑《收租院》创作组当时就明确提出“不要个人事业”、“不要个人突出”等口号。而当时盛行的集体创作形式与现代艺术的个性化追求绝不相容,更与“先锋”精神背道而驰。 正如当时所说,《人民公社食堂》、《收租院》、《毛主席去安源》不是一般的艺术创作,而是由上级组织布置安排的政治任务。从领导出题目,成立“核心组”,创作人员构思、制作,到集体讨论、通过审查,每一个环节都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的体现。作品的完成就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斗争的结果……。如果时过境迁之后,忘记或者掩饰这些事实,只能歪曲历史,误导不知底细的读者。 历史不会停顿。有一天人们会淡忘艺术品创作的具体历史环境,而艺术作品却有可能流传下去。一位理论家曾反问:“你会为秦始皇兵马俑的创作环境而否定兵马俑的艺术价值吗?” 这是一个排除了感情记忆的时空差异的提问。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完全排除感情因素的记忆和认知。秦始皇陵墓的随葬品对苟活于秦皇暴政之下的黔首,和对于两千三百年之后的消闲旅游者,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语录歌、样板戏对于当年的红卫兵,和对于当年的“牛鬼蛇神”,也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个没有这种感情记忆的艺术史家,对两种全然不同的反应和辩解如何判断,除了他的秉性、趣味之外,恐怕还要看他“史才”、“史识”、“史德”的高下。日本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学人在涉及南京大屠杀历史问题上,以感情记忆代替了理性的学术研究。这一立论的前提,即否认感情记忆在历史学中的意义,本来就极其可疑。何况更有人借学术研究之名,排除别人的感情记忆而大肆渲染自己的感情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