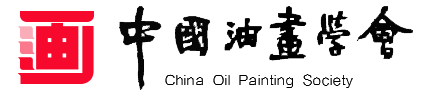水天中
| 现任: | 艺术评论家 |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
|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 |
|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常务理事 | |
|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
绘画的出现,源于人们企望保留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的视觉形象的尝试。随着绘画实践的积累和绘画观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重绘画形式自身的感染力,当人们对这种感染力的珍视,超过对其描摹事物形态的珍视的时候,作为艺术的“纯绘画”才算是诞生了。我们的先辈画家很早就走向这个天地,他们以特有的敏悟,运用单纯的水晕墨章,建构变幻无穷的绘画世界。古代画家以“无声诗”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一理想当然指向画家在作品中透露的精神境界,而达到这一境界的决定步骤,是他们像诗人那样,以极其洗练的方式对绘画形式因素的精心组织。中国绘画史上的那些杰作,在形式感和精神性两方面都与诗歌相通。而后来遭人诟病的陈陈相因,不是对绘画形式的过份讲究,而是对绘画形式的过度怠慢??以抄摹和重复代替了形式与意境的品味与拓展。 相形之下,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艺术遗产远不如传统绘画那样丰厚。从第一代留学生掌握西方绘画工具材料开始,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一直承担过多的社会性重负。能够涵泳于“绘画性”,徜徉于“无声诗”境界的自由光阴屈指可数。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们一直在各种重大使命之间奔波,而置绘画艺术自身于不顾。 从20世纪后期开始,这种状况有所转变,近三十年确实是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发展历程中前所未有的建设性岁月。文化封闭局面的突然结束,引发人们对外界艺术信息的渴求。与正常艺术史的发展不同,中国艺术家面对现代艺术百年流程,以自由采撷的方式各取所需。我们打乱了不同历史背景的阶段性艺术序列,于是出现了古今中西共冶于一炉的文化景观。古典、现代与后现代艺术图式、符号一起出现在当代中国画家的创作中。几代画家从不同方面,为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艺术性成长”作出贡献。 从形式语言的层面看,对绘画性处理的重视和对表现性风格的研究,是许多艺术理想并不相同的画家不谋而合的选择,这一选择对当代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品质的提升产生了推进作用。 对表现性因素的重视,是西方近现代绘画史上的重要动向。对表现性的追求,可以上溯到埃尔?格列科和伦勃朗,艺术史家甚至在米开朗琪罗雄强激越的风格里,追寻到“表现主义”的源脉。现代表现主义植根于19世纪晚期的浪漫主义,但在此之前,一些富于艺术个性的画家的绘画实践,已经将表现主义推上艺坛前沿。英国画家泰纳就是20世纪的表现主义出现之前,对绘画表现性作出淋漓尽致地发挥的人物。
提起表现主义,必然要想到20世纪初期德国的“桥社”和“青骑士”这两个艺术社团。这是两个具有不同目标的艺术群体,“桥社”的艺术家以激烈的变形展开社会性批判,这使他们的作品带有痛苦的表情;而“青骑士”们则潜心于新形式的创造,因此他们抽象性的绘画形式往往具有诗意。但这两方面的艺术作为,仍然不能涵盖表现性探求的全部内容。因为表现主义不是集中的运动,而是逐渐发展,并持续保持其影响的艺术潮流。它包括那些一直自外于各色艺术群体,保持独立身份,而在艺术探索上殊途同归的艺术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学院自然主义的艺术规范突围,追求个人思想、感情与视觉感受的直率表达。对传统绘画形体、色彩、构图等方面习规的反叛,使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在当时显得桀骜不驯,但他们的试验成为此后艺术家共享的艺术资源,不同追求的画家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不同的启发??诸如德国画家骚动不安的激情与法国画家对形式处理的敏感等等。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对表现性风格的亲近,有自己的文化心理背景。古代思想家对心性的参悟,传统画学对气韵、意境的追求,“书画同源”、“书画同法”的思路,文人写意水墨的成熟经验……这些分属不同层次的文化遗产(有些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心灵源流),为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的风格选择铺垫了文化基础。而对曾经作为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主导样式的通俗写实画风的厌倦与反思,更促使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向表现性风格靠拢。
前面说到20世纪后期,表现性风格如何成为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不谋而合的共同选择。历时性西方艺术现象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艺术家面前,是以共时性形态出现的。我们从历经数百年的西方绘画诸流派中认识了西方的“绘画性”处理方式,然后从“为我所用”的角度予以发挥。“绘画性”与“表现性”这两个交叉而并不重叠的概念,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并行不侔。 西方艺术史家曾经以明暗色彩造型和线条造型作为绘画性与非绘画性的标志。前者以提香、伦勃朗为代表,后者以波蒂切利、米开朗基罗为代表。但这种区分适应于哪些历史阶段,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中国的画家对“绘画性”的关注,不是由西方艺术理论的定义出发,而是从艺术鉴赏和创作实践出发。 在一般情况下,“绘画性”是对绘画形式本身的强调,是对绘画形式、技巧的某一元素的突出,是对画家在绘画过程中的个性、偶发性表现的肯定。至于大面积色域、光影造型、书写性(或涂刷式)的笔触、富于变化的表面结构以及构图上的交错拼接等等,都属于追求“绘画性”表达的不同手法。“绘画性”不是画得好,不是“基本功”过硬,而是画得舒畅,画得自由。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绘画性”的对立面是图像泛滥伴生的图像制作??往往是浑然一体无迹可求的制作。可以庆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对那些一心与照片争高下的细腻巧密失去了兴趣。 强调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对“绘画性”的认同与“表现性”的认同相仿,中国画家是在本土艺术潜移默化的基础上观察和试探“绘画性”的。在中国,文人画家即兴的作画方式和画家对点线韵律、水墨晕染的认识,使中国本土绘画具有明显的“绘画性”特色。因此,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对来自西方的“绘画性”这一概念的运用,属于“郢书燕说”式的误读,但只要对应我们自己的艺术环境,适应我们的上下文关系,符合我们自己的话语逻辑,并且有助于我们的创作,对这样的认识方式就可以给予肯定。 虽然中国艺术思想与“表现性”和“绘画性”有观念上的联系,但中国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并不是毫无阻隔地接近“表现性”与“绘画性”。在过去,绘画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表现性”风格一直被严加防范。只有通俗写实风格被认为是“正确”的艺术选择。在那样稀薄的空气里,林风眠、吴大羽、董希文、沙耆……依然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说他们“负隅顽抗”当不为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冠中以“快刀斩乱麻”(熊秉明语)的方式,为艺术形式辩诬,呼吁进行“创造新风格的美术解放战争”。从那以后,虽然批驳吴冠中几度蔚为风气,但中国绘画三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对绘画形式的追求的必要与可能。三十年来,中国绘画的变化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风格、形式的探索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与此前数十年的作品并置对照,就会看到画家在风格、形式方面的自由探索,对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艺术新面貌的形成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今天,“波普”戏谑之风,已经给艺术史上留下足迹的一切风格涂上小丑的油彩。而数字图像制作的普泛化,正在将人与绘画剥离。数码手段似乎是无所不能的,它以不可想象的迅捷毫无差错地完成一切,于是许多人从画笔、调色板转向鼠标和键盘。新工具的采用无可厚非,值得关注的是高科技图像对绘画的消解,高科技手段是否降低了绘画艺术中最可贵的因素,人的心灵敏感度。 历史背景与现实气候,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与绘画的关系。个体的智慧、感情与个体的局限在绘画中留下痕迹,而这种痕迹是无可替代的,绘画过程留下的理性与妄诞、激动与宁静、机智与笨拙、细腻与粗放、完美与不完美……这些是无可替代的。手艺与艺术的区别也表现在这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二十年来,有一批画家在探究绘画语言新的可能性,以表现性风格传达生命感受方面成效卓然。这本画册纂辑的作品,出自谢东明、阎萍、王克举、贾涤非、王琨、段正渠、井士剑、任传文八位画家之手,他们正是这方面风格探求的代表性人物。
也许是一种巧合。八位画家都出生在1956?1963年间。在那几年里,中国人经历了解冻的早春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清算;大跃进的狂热与随之而来的全国性饥荒。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文化荒芜与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复苏,使他们在成长期就习惯于比较、判断和思考。与成长于其他年代的人相比,这一代艺术家常常表现出与旷达相伴的沉重,早岁经历又使他们对艺术的爱好特别执着。在艺术上呈现的感情沉厚与形式自由,与他们艺术成长的背景有关。他们的前期作品与同辈画家相仿,有较多的叙事因素,后来转向表现性风格。这里着重讨论他们在绘画语言方面的表现。 谢东明画风酣畅有力,用古代书论的说法来形容,就是“风樯阵马 沉着痛快”。简括、突兀、开门见山的构图;时而行云流水,时而刀砍斧劈的笔触;饱满、响亮、厚重的颜色……他将关键性的绘画因素推向极致,对可有可无的“闲言语”则果断地丢弃。值得玩味的是他这种画法不但没有简化作品的精神内涵,反而使他笔下的人物、静物和自然具有神秘、多义的表情。 阎萍以她的“母与子”系列引起美术界的注意,她对绘画性的追求,曾使许多美术家感到激奋。她以具有鲜明性格的笔触,创建出一个充满了不停变动的色彩与阳光的天地,使习惯于沉重的形式与压抑的情感的中国观众,感受到艺术与人性中欢快明朗的一面。近年她将视线转向传统戏曲演员的生活环境,那里的形态、动作、色彩、情感使她更加自由地施展表现性绘画手段。阎萍的艺术展示了我们文化中不为人看重的开朗、自由和绚烂。 王克举近年的作品以风景为主,既有高远的山岳和林木,也有疏落的草卉与庄稼。评论家说他进行了一场“风格反叛运动”的话,这种“反叛”的目标是建构符合个人心性的绘画形式,而“反叛”的动力来自拥有无限生机的自然。在开阔野旷的地方对景写生,是他最喜欢的作画方式。他以这种方式亲近自然,享受艺术创造的乐趣。与大自然交流生成的激情,与构成、节奏、形、色、笔触一起在画面上生长。 贾涤非是中国表现性画家的领头人之一,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以个性化风格挥写对生命和自然的想象。富于刺激性的色彩、繁密而流动的线条,构成难以捉摸的奇异场面??在那既“现实”又“超现实”的场面中,包含着他所说的“诗人心灵的震动和幻觉”。他的表现性语言和图式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但他表现生命在纯朴的自然或深奥的文化环境中显示的无穷活力,始终为后来者所难及。 段正渠以单纯而强烈的手法表现山乡男女的粗犷和率真,以及在粗犷率真中透露的丰富人情。在粗壮的线条、深重的背景和形象的简约等方面,他借鉴并发挥了鲁奥的庄严与神秘,又以陕北高原的朴实温情改变了鲁奥的阴沉和忧郁。在中国土地上,贫瘠的陕北高原是一块极具“表现性”的人文环境,段正渠所营造的形式系统与他所表现的人文环境,具有相同的气质和韵味。 说到王琨,就会想起王琨笔下的牦牛。我与牦牛、雪地都曾有过相当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所以能够有把握地说王琨画牦牛不仅得其形色,而且得其神气。“神气”的获得与画家的表现性形式不可分,那种不拘小节的浑朴,融合于浩渺天地的形体处理,既洒脱又拖沓的笔法……使“深入”和“完整”全成多余。而熟悉他的朋友很自然地由此联想到画家之为人处世。 井士剑是难以捉摸的??他的艺术给人留下各种对立的印象,严峻的深沉中会冒出玩世不恭的气泡,典雅的形式下可能深藏着嘲讽的的冰层。但即使不同艺术信念的人,也很难轻易否定他的作品,因为他对现实人文环境有深入的思考,在绘画形式语言方面有过人的颖悟。在他对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形、色、笔触、肌理的调遣中,可以想象这位艺术家在“存在于虚幻之间的漫步”(龚云表语)。 九十年代初,初次登上画坛的任传文,以他深邃清新的作品感动了许多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家。人们在他的画上“发现”了一个十分普通而又十分神奇的天地,那是现实和梦想相融相汇的境界,是“神与物化”的痕迹。物象的平凡与思致的缥缈,可以说是任传文创作的特点。而体现在画面上,平凡与缥缈都依仗恰当的形式存在,任传文所说的“纯化感觉,迹化感情”,正是对这一相反相成关系的概括。 不久前,在讨论作为艺术的绘画是否消亡时,我曾说过,凭借人类自己的生命机能(心灵通过眼睛和手)保留来自外界的视觉感动,是绘画存在的基本理由。绘画的形式及其表现性反映着人的生命特征,只要人类的生命延续下去,这种心灵感动和技能就必然存在。 我不反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说法,当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消失的时候,艺术以及其他型态的文化以至于人类的历史都将随之消亡。而在人类继续存在并发展的今天,艺术。绘画不会消亡,它仍然在发展。这一乐观看法(严格地讲,这只是对具体的有限事物的乐观看法,而不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乐观看法)的根本前提,就是艺术家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发挥心灵通过眼睛和手,保留我们视觉感动的乐趣和努力。而这正是我赞美八位画家的基本出发点。
己丑上元日于京北立水桥
此文为《绘画的行进?中国表现主义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八人展》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