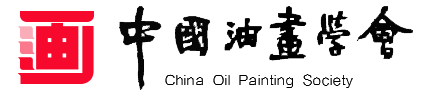邵大箴
| 现任: |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各种艺术创造中呈现的所谓“美”,不论其通过何种表现形态和表现方法,其内容都有其相通的一面,也就是说,美的内核即精神是共同的,但因各有其特异的审美追求而别具风采。就西方近代以来的绘画而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和其他各种现代流派,都各有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它们不会因为时代变迁所造成的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失去其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特异的审美追求使艺术园地愈来愈绚丽多彩,也使人们的艺术体验和享受愈来愈多样,愈来愈丰富。艺术欣赏中有许多有趣和值得人们思考的现象,其中之一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审美标准和欣赏趣味的普遍性和差异性问题。应该说,普遍性、共同性是主要的,但不能忽视实际存在的差异性。由于有普遍性,凡是好的艺术品,不论产生于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能为人们欣赏:因为有差异性,不同的民族因审美习惯有所不同在选择作品时自然会有所偏爱。举例说,在欧洲近现代绘画流派中,法国的印象主义在中国艺术家和中国观众中,有很多知音,有很多仰慕者。凡是介绍法国印象派的画册和书籍在中国历来畅销,几次来华的法国展览中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都受到人们的特别注意。倘若要问,对现代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影响最大的欧洲绘画流派是哪个派别?恐怕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是:印象主义。为什么印象主义对中国艺术家和中国观众有如此大的魅力,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可能这与印象派的审美趋向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有某种相互呼应的东西,本文试作简略分析。 众所周知,欧洲艺术虽有希腊与希伯来的不同传统,但在20世纪之前其主导方向当属在古代希腊即已形成的写实体系。欧洲写实体系的美术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为世界所注目。而在东方,尤其在中国,艺术的主导方向为写意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大体系并非完全对立、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的。实际上欧洲的写实体系中也含有写意的成分,在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东方写意体系中也含有写实的因素,这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两大体系的艺术以自己的审美趣味不断熏陶、训练和教育着自己的观众,使他们形成某种欣赏习惯。中国写意艺术体系强调艺术家的主体性格,重视艺术家自己的主观感受。在语言表现上讲究形神兼备、以形写神以至以神写形,不拘泥于形似和不拘泥于对客观物象的真实再现。写意艺术更注重通过诸形式因素如笔墨、色彩,如绘画的点线面来表达作者内心的感情。写意体系的艺术在情与理之间更重视情,尤其在文人水墨中,感情的表现更率真、自然。为此,作品创造过程更强调一气呵成,强调即兴式和自由发挥、因势利导,甚至“将错就错”。 当然,写意体系艺术注重的自由与随意,也需要有“基本功”的训练方可获得,不过这种基本功不在写实造型,而在于艺术家全面的文化修养,所以中国的文人水墨画强调功夫在“画外”。对水墨艺术来说,“画外功”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对人生、对自然的体悟,也就是说对人生和自然的理解和认识,要达到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境界,要把艺术作为自己人格物化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写意的艺术家一生都会处于“修炼”之中。在语言技巧上,属于写意体系的文人画家的“画外功”最重要的是“书法”,因为这种画是“写”的艺术,“书写性”是它的基本要求。“书写”有别于“描摹”,在书写中线的一波三折,手通过笔的运转所用的全身的体力、臂力和腕力,通过提、压和拖,诉诸于画面各种痕迹。这些痕迹表现于线,也表现于皴擦点染之中,它们既是艺术家作画时的情绪的直接反映,也显示出艺术家的气度与胸怀。 中国艺术家和广大观众最早接触的是欧洲古典的写实艺术。写实的艺术在中国人当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仰慕者有之,贬损者亦有之。仰慕者在欧洲古典写实中看到了中国文人画中所缺少的反映客观物象的“形”,这派人士认为形不在,意焉能存?他们竭力主张中国人学习欧洲的写实艺术,认为引进欧洲写实艺术是使中国艺术走向人生、走向现实的惟一道路。贬损者认为,欧洲写实体系太尊重客观的视觉视实,不能充分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感情。中国应保持本民族写意传统,他们认为中国接受欧洲写实主义是把艺术引向歧途。这种争论在中国延续了近百年,很难说这种意见分歧如今已不复存在。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在中国艺术家和观众中引起的波澜更大,争论的时间也更持久,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不过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讨论,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和观众对欧洲古典艺术和现代主义的认识已经更为全面和科学,态度也更为冷静与理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现象是,中国人对介于古典写实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印象派艺术很早就持有另外一种态度,那就是承认和赞赏。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现代艺术家中有不少人曾专门撰文介绍和评价印象派,或在论艺的文章中涉及到印象派,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印象派艺术的特色,并试图把印象派艺术与中国艺术作比较。写这些文章的有较早接触西洋画的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倪贻德、丰子恺等人,也有专门从事传统水墨画创作的国画家。在前一类画家中对徐悲鸿、林风眠的意见最有代表性,而在后一类画家中两位山水画大师黄宾虹、李可染的看法颇值得我们重视。 20世纪30至40年代,在对中国艺术前途有不同认识和分析的徐悲鸿、林风眠(他们都曾游学法国)对印象派都持肯定和赞赏态度,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出发点也不尽一致。徐悲鸿虽然批评马奈(Manet)的“俗”、雷诺阿(Renour)的“媚”,但他重视印象派的写生和他们当中注重素描造型的艺术家,如德加(Degas),又对印象派中在运用色彩方面颇有造诣的画家予以肯定,说他们的画也是重神韵的。1947年,他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文中写道:“印象主义出,绘画上亦重韵律,其中钜子如莫奈(CloudeMonet)、西斯莱(Sisley)、毕沙罗(Pissarro)均以密点敷彩,放弃线条。较大小米尤精妙。”(“大小米”即画史上通常说的宋代山水画家“大米”、“小米”父子,大米即米芾1051-1107,小米即米友仁1074-1153,他们在师法造化的基础上创造出烟云变幻、苍茫朦胧的“云山”之景-本文作者)认为这些可供中国艺术家们借鉴。而林风眠则从绘画革新的途径上对印象派的贡献加以肯定。他说:“法兰西在19世纪里,艺术上发生了三次影响遍及于整个世界的大运动,第一次是浪漫派,第二次是写实派。第三次就是印象派。”他还说:“我们追溯印象派形成的原因,就必须提到中国和日本。”他在比较了中西绘画表现山水风景的历程之后说:“西洋的风景画,自十九世纪以来,经自然派的洗刷,印象派的创造,明了色彩光线的关系之后,在风景画中,时间变化的微妙之处,皆能一一表现。而且注意到空气的颤动和自然界中之音乐性的描写了。我们觉得最可惊异的是,绘画上的单纯化、时间化的完成,不在中国之元明清六百年之间,而结晶在欧洲现代艺术之中,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陈列在我们目前,我们应有怎样的感慨。”由此,林风眠主张中国绘画从传统、摹仿和抄袭中走出来,尽量吸收西洋绘画贡献出来的新方法。他认为应从三个方面着手:1、在整体的把握复杂的自然物象中,寻求绘画上的单纯化,而不是依靠文人随意的几笔技巧去取得这种单纯化;2、改进绘画的原料、技巧和方法;3、绘画的基本训练,应采取自然界为对象,绳以科学的方法(《中国绘画新论》,1929)。 黄宾虹是通过画册接触到印象派艺术的,他当时正在探索通过积墨法来取得画面丰富、厚实的效果,他凭直觉领会到印象派风景画与中国山水画的接近。他在书信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欧风东渐,心理契合,不出廿年,画当无中西之分,其精神同也。” (《致朱砚英书》,1943年)李可染得益于印象派的主要是逆光描写,他结合从伦勃朗绘画中吸收暗中透亮法的同时,又用逆光法使自己的山水画面貌为之一新。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中国有很伟大的艺术、艺术家,外国也的确有很伟大的艺术和艺术家,如伦勃朗、莫奈、雷诺阿……” (《让世界理解东方艺术???最后一课》,1989.11.24在师牛堂谈话)从这简短的谈话中可见他对印象派画家的尊敬。从上述中国艺术家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之所以对印象派的艺术感兴趣,不外乎有下列原因:
一、印象派画家有严谨的基本功,但不拘泥于写实,很注意在笔触的自由、潇洒中表达情绪,表现神韵,有相当的写意性,这与中国人欣赏趣味相通。
二、印象派从日本、中国艺术中吸收了营养,在表现语言上追求绘画的平面性、装饰性,使中国人感到亲切,也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三、印象派的直接写生,补充了中国晚期文人画的不足,但印象派的写生强调写印象、写感觉,这一点与中国画的理论不谋而合,中国画家也乐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