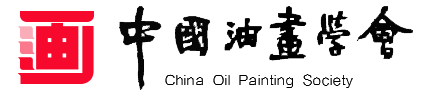刘建平
| 现任: | 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理事 |
|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院教授 | |
|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对于我,高碑店的教室是有“语言感觉”的地方,四个方向水泥墙壁环绕着模特儿,窗口过来北方的散漫光照,不暖也不是很冷。对象很“空间”,很清晰;早晨,打扮和收拾过的学生或模特儿,带着冬天户外的粉尘,从或远或近的住处来到这里,教室里,很宁静很“常态”也很“风尘仆仆”。
模特儿坐在那里,通常是显得疲惫的样子,身上的主要部份按照规律相互支撑,并且共同依赖了椅子和椅子下面的地面形成了一个便捷的“坐”的“状态”。如果我是模特儿,会当成一次旅行中乘坐了长时间的列车,可以心安理得于无所事事的感觉,这只是我的感觉或者我的爱好,不一定是模特儿的感觉,他或她完全可能是另外的需要和想法。事实上这些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她们的形而上,或许也就正好特别乐于坐在这里,就正好和我在长途的列车上面一样。
一个不能被揣则的感觉系统和想象世界正是一个人、一个对象、一个模特儿最精彩的东西。也正好是我们自己无论怎样贪婪都不可能获取的东西。我们所能有的,只是面前这个对象可以观看的部份,和对这个坐着的、形的“状态”的反应。我的“现代意识”基础、“文化”观念和人的“自尊”的观念,以及“专业”立场都与此有关。
我想到安基里柯,想到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有安基里柯壁画的那些房间,那些一张床,一件家具和一幅壁画的简单小屋。接着又想到具有相同观感的延安窑洞领袖住所,就我的印象,延安那里也是一张床,一件家具,一件椅子或一件板凳。实际上长期以来,是这种简洁、明净和朴素之感常常使我心旷神怡,不仅长久影响了我关于幸福生活的意识和态度。而且常常说明着我的体验和状态。
我还感觉到了“粉尘”这种东西,“粉尘感”是我最近以来的发明。如同光照一样,尘也无所不在。尘的“意味”,诗和词的古人今人有过特别动人的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个意味和表现的动人,尘就特别被“文化”了。对于我的感觉和实践,尘是“观看”的结果还是“文化”的力量不是有意义的问题。只有一点,是尘的感觉提示和丰富了我对人物的观看,尤其是属于“怜见”那一面的观看。人有了尘的一面才显得可爱,所以我说过对人的尊敬和热爱与日俱增,这一成果要归于我的“尘”之发现和体验。
我估计,我的画或许逐步在注解以上这些。换过来说,以上说法就是我画的注解。
《工农兵系列》,是以另一种情况观看和指认人的状态。同时与我对图画及其照片“语言感觉”的兴趣有关,这是些“间接”材料,但一直是我周围的“存在”,以至于成了我感觉结构中的重要东西。图片或文献的“文化”,已经在我“自我”的感觉和心性中,不能分离。
另一方面,以上这个意思,并不意味着我逃避现实。实际上我画的不算历史,同时,也不认为虚构更有意义。一切当中,现实不仅作为资源,而且是基础和支撑。问题在于我认为现实是一定时间段落,现实感之获得又往往通过“媒体”;这样,我这里的现实就不能和文化分开,“现实”是以一个复杂的样子和结构面对着我。这样,我的“现实”感,往往通过“语言”获得,或者说通过“关于现实的语言”与“现实本身”的相互认领和反衬而获得。
为了能清楚说明这个问题, 我想举出我看军事博物馆一个展览,叫做《复兴之路》的例子:一、我;二、大量的抗日照片;三、几件延安和根据地的木刻作品。对我而言,假如画我们习惯上的历史题材绘画,中间又缺少了根据地生活的直接经验,照片就作为资料呈现,我则研究作为资料的照片;然而我不画这种历史画,我的趣味在这些图片感觉,对我而言,图片在我面前的事实就是现实,同我看到的模特儿一样,这张平面的照片有它自己的语言感觉。再比如我和根据地木刻之间,我在意的不是通过它们了解当时的革命和生活,也不是要体会当时艺术家对生活的概括,现时这两点对我都不够重要,我的指向是在木刻本身的语言意思。我深感“语言感觉”这种东西同样激动人心,简单不过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语言感觉的体验”传达过来,也可以说是表达一种“文化”的语言感觉,只不过这种文化的“现象”就是我面前的照片和木刻;这里的复杂情况是传达这种感觉的手法,及其与“关于语言感觉的语言转化”相关的其它课题。也是重要的、有难度和实践性的课题。
由此出发,我一部分画取材于上个世纪六十或者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形象,重心在于图片本身与我感觉和心性的联系,我虽然经历过了那个时候的直接生活,但是既没有兴趣又不记得多少。我只是从小看惯了图片,图片本身就很直接,同时它又有和我的童年感觉凝结起来的无比亲切。《工农兵》对我而言,就是照片或雕塑上那些,我不会把任何具体人作为工农兵中的某一成员。
在这样的“语言感觉”环境中,我的意识和语言探讨才显得明白,我的文化感觉和现实态度才显得明白。在现时,我的感觉框架和语言框架就是这个状态。
我陈述近期实践环节中的一部分思想活动,把这些东西并置在上,目的是在实践角度强调观看的重要和对观看的表达,附带强调与此相关的感觉系统的意义,与我自身的专业化要求有关。其实观看也不应该是被“特别”强调,强调过了就不太自然,只是无奈于当代语言文字等等的浅显表达过于容易和牵强附会,以至于“观看”的位置一退再退。事实上,“观看能力”对于人本身意义重大,但是首先要能够“注意”。我不希望同时代的人们由于看的东西太多,匆匆忙忙之中忽略了特别有价值,更加灿烂的部分。我们本应该感谢现代社会,既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看的材料,又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有助于看的硬件条件,“看”就应该有更加深入的内容才对。此时,我想到塞尚和康德,他们以特别专业化的姿态,为“观看”或“思想”表现的深入作了最本份的贡献,他们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此时我们也看到帕穆克,看到他对于感觉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描述,体会“人”和精神表现之软件质量和可以深入的空间,他就生活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发表于2008年《星艺术》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