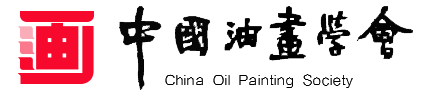《回望家园》--乡土现实主义回顾
阅读:549发布于:2009-06-22 00:00 作者:中国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学会
中国现代艺术的伟大转折在艺术上是基于两个深刻的背景,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对前者来说,是文革的灾难唤醒了人民,现实主义回归的主要基础就是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因为十年动乱的灾难就是人性的曲扭,人的尊严与价值变得毫无意义。艺术的本质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摹写,而是人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审美的形式中实现自我的方式。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能在自己所创造的形式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但是在建国后的几十年艺术发展中,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政策限制下,艺术个性与形式创造被遮蔽了,艺术家从事艺术工作只是在掌握了一定的绘画技能后,形象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因而形式上的千篇一律在所难免,而有意追求形式感的艺术家也会受到严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技法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与这个新传统是分不开的。
中国新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变以现实主义的深化为标志,这种深化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方面是继续深化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但不再局限于文革的情结,而是向更广阔的现实、更深层的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开掘;另一方面是以独特的观察角度来反映现实,在艺术手法上更多地借鉴了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这些手法对很多艺术家和广大观众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它们不仅更有力地表现了主题,而且还突破了俄苏绘画的模式,为自由地借鉴西方现代艺术开了一个先例。
无论是“反思”还是“伤痕”,历史终究要翻过这沉重的一页,否定文革,批判四人帮的目的还是要告别旧的时代,建设新的生活,现实主义的目光最终要回归到生活的现实,我们的落后是因为世界上前进。国门打开后,大量的信息奔涌而来,每一个艺术家可能也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思想上所遭受的沉重撞击还不是艺术的思潮,而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重新认识我们的现实,认识我们的国情,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这个责任的沉重一点不逊于对文革的反思。
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系研究生陈丹青到西藏去了半年。在那儿创作了6幅画,回北京后又画了1幅,然后命名为《西藏组画》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画幅不大,都是描绘普通藏族人的日常生活。他凭着自己的感觉,根据对生活的细心观察画出的7幅小画一经展出,便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并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单纯从画面上看,《西藏组画》确实是对现实的直观,但在这现实之中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从来不可能在艺术上表现的真实。那些粗犷沉默的康巴汉子取代了豪情满怀的工人和农民,贫穷而表情木讷的喂奶妇女也不是在很多美术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翻身农奴的妇女形象,尤其使人怦然心动的是那个朝圣的场面,虔诚的人们全身匍匐在地上,沉浸在宗教的狂迷中……对很多人来说,陈丹青的这种表现手法是不可思议的,艺术应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应该向人们展示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怎么能这样来表现生活的沉重、阴暗与迷信。陈丹青认为他只是画了他所见到的真实,7个作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效力,并不依艺术家本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正是从这组作品中看到了贫困与愚昧,而又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蕴藏在其中。虽然陈丹青画的是藏族题材,但人们更愿意从宽泛的历史角度来理解作品的主题含义。首先,《西藏组画》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性,一扫美术界沿袭的戏剧性与唯美主义的传统。甚至在“伤痕”美术中,除了对文革的激烈批判外,在绘画语言上并没有人的突破。这种真实性既包括一直被作为禁忌的题材,如贫困和愚昧,也包括视觉上所造成的现场感。那种像抓拍照片一般的构思,对传统的对剧性构图来说是一种不完整感,但却使观众有亲临现场的感觉,把观众放到了目击者的位置。在一个谎言充斥的时代,真实就是对现实的最激烈的批判。此外,真实除了自身的意义外,它所表现的事实还涉及对社会更深层的思考,“伤痕”美术涉及的还只是文革的具体事件,而《西藏组画》则使人联想到产生文革的根源,那种封闭、麻木与愚昧的国民性不正是文革的社会基础之一吗?
《西藏组画》在美术界产生文泛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表现形式上的突破,这种新的表现手法一方面使真实性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写实规范。长期以来,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已经习惯于选择一个戏剧性的情节瞬间,再构造一个以这个瞬间为中心的舞台效果。在《西藏组画》中,没有一个场面有着戏剧性的冲突,只是把画家眼前所看到的东西直接搬上画布,有些画面在构图上甚至还把主要人物直接朝向画面的边框(如《赶集》),这种对构图规范的有意破坏却强化了画面的现场效果。陈丹青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上的尝试主要是受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影响,在色彩和笔触的运用上尽量朴实,那种深厚的灰褐色几乎是画面上唯一的色彩,加上涂抹效果的笔触,使画面有一种凝重感。当时中国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虽然摆脱了文革时期的“红光亮”色彩,但俄罗斯画派的银灰色调和摆放成块的笔触还被认为是基本的造型语言。欧洲着名的美术史家沃尔夫林(瑞士)在他的名着《美术史原理》中曾说过,陈旧的破烂的东西比平整光滑的东西更有绘画性。陈丹青充分发挥了他的技法,才使得“贫困和愚昧”这样的题材得以显现出来。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契机,陈丹青获得了题材与形式的双重突破,在题材上他由对具体事件的反思发展到更深层的文化反思,在形式上体现了一种非学院化的倾向,为正开始出现的多元化形式的追求树立了一个样板。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主题为美术界所关注,他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绘画语言上的问题不容易为圈外的舆论所关注。而同样被誉为中国现代艺术里程碑的《我的父亲》(1979)则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这幅画还经常被一些文艺理论与美学论着作为艺术分析的范例。 《我的父亲》(这幅画后来的美术界内外被简称为《父亲》)的作者罗中立当时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这幅画先在四川美院学生画展上展出,然后参加了四川省青年美展,并在全国青年美展上获一等奖,随着报刊的大量刊登和好评如潮的评论,《父亲》已成为新时期美术的一个象征。《父亲》的形象也成为文革后现实主义美术的一个高峰。这是一件巨幅作品(217×152厘米),整个画面只有一个老年农民的脸部及画面下方显露出来的半只手和半个盛着水的破碗。这幅画的题材来自一个偶然的契机,在一个寒冷的除夕之夜,作者在家附近的一个厕所旁边看到一个蹲在墙角等收粪的中年农民,与陈丹青不同的是,罗中立没有把这个场面如实地记录在画面上,而是在巨大的画幅上只刻画他的画部,那种强烈的视觉效果会使每一个观众在他画前都能看到他暴跳的青筋、刀刻般的皱纹、从细小的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以及干裂焦灼的嘴唇,听到他沉重的喘息,闻到他特有的烟叶味和汗腥味……
毫无疑问,罗中立的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是受了美国照相写实主义的启发。他曾说过,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美国照相写实主义的图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感到这种形式最利于强有力地表达他的全部感情和思想。照相写实主义属于美国波普艺术后期的一种风格,其主要特征是用精细的笔法将彩色照片放大成巨幅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其制作方式完全是工艺性的,采用九宫格与幻灯机或投影仪来放大照片,作画的过程完全是冷漠的、机械的,但画面色彩艳丽,场景和形象都极其逼真,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加上画家精心选择的题材,使这种风格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含义,如其代表人物克洛斯画的那些巨大的人物头像,在冷漠的表情下掩盖着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异化,尤其当观众站在这种大画的前面时,更是感觉到这种冷漠扑面而来。正如罗中立对这种形式的理解一样,如果把《父亲》的画幅缩小一半,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当然,罗中立并不完全照搬照相写实主义的样式,他主要吸收了其中的大的尺寸和构图的方法,但不是那种机械的工艺性的制作,而是按照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基本画法,运用色彩和笔触塑造出了“父亲”的形象。而且,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非主题的商业化风格,而《父亲》则继承了现实主义绘画的传统,表现了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
那个“又脏、又暗、又涩”的“父亲”的形象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审美范畴,即便他是“丑”的,也是我们的父亲,谁应该对他的苦难负责?谁又有权力来隐瞒他的苦难?《父亲》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三中全会以后,震撼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正起于这个时候,农村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正因为“父亲”处在贫困的最底层,经济改革才首先以农村为突破口。《西藏组画》和《父亲》标志着乡土现实主义的出现,在此后的几年内,它几乎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主要流派,强劲地冲击着中国画坛,当时正在逐步深入开展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改革构成了乡土现实主义的大背景。
《西藏组画》和《父亲》给人的感觉是沉重和悲怆,而另一件乡土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春风已经苏醒》则给人带来美和希望。以画知青题材而初露头角的何多苓以一种凄美而又不失希望的诗情创作了《春风已经苏醒》(1981),为乡土现实主义风格树立了一个典范。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一个衣着破旧的小女孩,坐在初春长满枯草的河滩上,迷茫而又深情的目光遥望着远方,春天的微风吹动了她的黑发。这个完全写实的画面却暗含着寓意,苦难即将过去,希望正在萌生,就像春风吹拂过的荒原,必将是绿色覆盖的原野。此时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伟大变革的转折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多地区立刻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对于有过插队经历的知青出身的画家来说,对这种现象的感受尤为深刻。何多苓就是如此,他在创作体会中谈到:“我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早已告别了那个世界,但它并没有在我心中消失。相反,每当我想要画点什么的时候,它就如此清晰地展现在眼前??那是个贫的地方,光秃秃的山坡,荒凉的河滩,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东西;天空淡漠的瞧着大地;……”显然,何多苓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赋予它特别的含义,他只是画自己经历过的生活,那种贫困而又纯朴的生活使他久久不能忘怀,可能他就是要画出这种记忆但又对那片土地寄予希望,画的标题就说明了这不仅仅是回忆。
在美国30年代的现实主义运动中,有一个被称为地方主义的流派,主要画美国的小镇风情,其中有个初出茅庐的画家名叫安德鲁?怀斯,以伤感的情调描绘乡村的生活场景。怀斯画了一辈子这种题材,他的笔下永远是偏僻农场,萎萎荒草和孤独的人,形成一种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在都市文化与消费文化席卷全球的时候,怀斯的艺术具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顽强地固守最后一片精神家园。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他的绘画风格也显得冷峻而理性,每一个形象,每一处景物,甚至每一棵小草都描画得极其仔细,这种风格无疑使正在现实主义风格中寻找出路的中国写实画家有了样板,尽管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艺术,而只是看重他的技法。当人们看到《春风已经苏醒》的时候,很自然地联想到怀斯,那片荒草地,那个孤独的女孩……何多苓直言不讳地承认怀斯对他的影响,他说:“我的确很喜欢这位‘伤感的现实主义者’,并且试图摹仿他。我喜欢怀斯那严峻的思索,他那孤独的地平线使我神往。”显然,何多苓从两方面接受了怀斯的影响,一是那种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从一个普通的画面中喻示了深刻的哲理;二是怀斯的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技法,尤其是他表现服饰的质感与草地的效果,在何多苓的画中得到完整再现。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何多苓不可能看到怀斯的原作,而是根据印刷品的印象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画法。
继何多苓之后,在乡土现实主义中掀起了一股怀斯画风,这不仅是因为怀斯本身就是一种乡土现实主义的风格,他的一些效果可以直接搬用到中国的乡土题材中,也因为当时的写实画家大多接受的是俄苏学院派风格的训练,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既想坚持原有的写实风格,又想有限度地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风格,这样,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写实绘画往往成为青睐的对象,如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超现实主义、美国照相写实主义、怀斯及加拿大现代画家柯尔维尔,甚至欧洲美术史上的一些画家也成为借鉴的对象,如16世纪的西班牙样式主义画家埃尔?格列柯和法国17世纪的古典主义画家拉图尔。可以说,在当时的乡土现实主义绘画中,几乎都能看到西方传统与现代绘画的影子。
进入80年代以后,乡土现实主义已成为中国写实绘画的主流,这也是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时的一个独特景观。罗中立在完成了《父亲》之后,继续画了《春蚕》和《金秋》等大型作品。随后是乡土系列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故乡组画》,直到90年代,罗中立还在不懈地画农村题材,只是在风格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写实的再现逐步向民间艺术的风格转变,程从林继《1968年×月×日,雪……》之后,又创作了一幅大型作品《1978年夏夜,我看到一个民族的渴望》,此后也进入了乡土题材,他主要是表现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风情,他吸收了一些埃尔?格列柯的光色效果,再加上他在制作上的一些创新,使他的乡土题材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感觉,这种手法在当时影响了很多年轻画家。其他四川青年画家如朱毅勇的《山村小店》、张晓刚的《天上的云》、周春芽的《剪羊毛》和杨谦的《喂食》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乡土现实主义作品,而且都是在走向乡土的过程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风格,如张晓刚的《天上的云》就大胆吸收了凡高的用笔,对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的写实风格相结合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在80年代前期,乡土现实主义成为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创作的重要题材和主流风格之后,逐渐越出了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范围,在其他艺术门类中也有所反映,并且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与作品,构成了乡土现实主义的宏大景观。从整体上,乡土现实主义的发展向着两种倾向发展,其影响一直延伸到90年代初期。这两种倾向分别是学院主义和原始主义,前者最终与新古典画风相结合,后者则融入了前卫艺术运动。
学院画风的乡土现实主义在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上有充分的体现,如果我们把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和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作为乡土现实主义的原型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出学院主义与这些原型之间的重要区别。对后者来说,前者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首先是有着强烈的现实与文化批判的意识,它们属于思想解放运动在美术界的反应,唤醒人民对现实与历史的沉重思考;其次是这些艺术家在形式上都大胆吸收了西方近现代艺术的影响,而不是拘泥于课堂上接受的那些基本技法的训练,这些形式本身也构成对学院训练的挑战,当然,一旦这些技法成为正统之后,也逐渐成为一种学院的规范。学院主义与之有着重要区别,首先这些艺术家大多没有明确的批判意识,他们对乡土题材的选择或者是出自个人的农村经历,或者是为自己偏爱的技法寻找合适的题材。其次学院派的基础几乎成为他们创作的基本准则,这种倾向在新古典画风中反映得尤为明显。但是,学院主义在当时并不是消极的。因为各个学院艺术在当时也正是一个转型期,即从传统的俄苏模式向更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教学方式转变。在清理文革时期对美术学院教学秩序的破坏的同时,美术学院也在建立起新的教学秩序,如在当时关于恢复裸体模特儿教学的问题,就是在美术界涉及思想解放的一场大辩论。但是学院作为“主义”来理解与教学还是有重要区别。在学院主义看来艺术的技能是最重要的语言(欧洲传统的学院主义还包括学院规定的题材,如古代神话和圣经故事)。任何题材首先要适合技能的需要。在新时期初期,处于转型期的学院绘画与乡土现实主义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即从适合主题性情节性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俄苏模式转变,这个过程也是一场革命,虽然不如乡土现实主义来得那么激烈。
学院画风的乡土现实主义是在乡土现实主义的影响日益扩散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身也属于乡土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它的技法更为细腻,乡土情调也更为浓郁。由于传统的关系,具有雄厚教学实力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这种风格的中心。50年代的马克西莫夫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训练班就办在中央美术学院,这几留苏归来的学生也较其他院校为多,注重基本功的训练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的一大特色。“文革”以后,最早以扎实的素描基础为其造型语言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就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教员钱绍武。当时在版画系就读的学生吴长江在素描上就深受钱绍武的影响,然后他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细腻深入的风格。吴长江的毕业创作是石版组画《藏区组画》,在全国“三版”展览上获得普遍的好评,当时就有人认为吴长江的素描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在石版画上所达到的素描效果在全国却是少有的。吴长江的创作题材主要来自青海藏区,他被藏区苍茫的自然景观与藏民的艰辛劳动生活所吸引,但他没有像陈丹青那样着重挖掘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那种精神力量,而是以细致的观察与体验来如实地记录一个个劳动生活的场面。以素描语言为基础的石版画的绘制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过程,不可能像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那样把即兴的情感通过笔触带入画面,吴长江充分发挥他在素描上的功力,以大量的藏区写生和摄影照片为基础,对素材进行深入的刻画,创造了一种宁静而又凝重的效果,尤其对草地、牦牛和藏民的毡袍在质感上的表现,更是具有其他绘画门类所难达到的效果。如《挤牛奶》(1981),画面没有正面的人物形象,只有一个背对画面的女牧民在弯腰挤奶,白色的雪地和天空衬托出黑色的牦牛,黑色的牦牛又衬托出穿着灰白色毡袍的藏民,画家通过素描特有的处理方式简化了黑白照片的层次,显得明朗通透;而雪地、牦牛和衣袍又具有照片所不及的质感,素描的语言与画家对题材特有的理解方式融为一体。吴长江不仅丰富了石版画的语言,同时也创造出一种宁静、悠长而又辽远的意境。
同在中央美术学院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系读研究生的孙为民也是80年代中期乡土现实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在传统学院派技法的支持下努力画出自己对乡土的一片深情。从这个角度看,孙为民比较接近四川的画家,像何多苓那样农村的经历是抹不去的记忆,不同之处在于孙为民更加朴实,他甚至使人面对着他的作品时会淡忘他的技法,直接面对生活本身。孙为民在文革开始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然后在河北蔚县的一个偏僻农村了度过了三年青春时光,与同代人相比,孙为民是接受过艺术训练之后再去农村的,所以他在经历农村的贫困和农民自然朴实的本质的同时,也就能够以艺术的思维来记录自己的切身体验,农民的题材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农村题材是从他的生命中浮现出来的。在他的大量创作中很多是没有人物的风景,这些风景是从写生中提炼出来的,成为独立的风景画创作。这种样式虽然后来成为风情画的重要样式之一,但孙为民笔下的农村风景却凝聚了深沉的情感和个人经验的记录,这是那种风情化的农村风景画所远远不及的。 《歇晌》(1984)画的是一个简朴的北方农村院落,透过树阴的阳光斑斑驳驳地照射在墙面和歇卧的黄牛身上,浅浅的银灰调似乎是从记忆中把这个如梦的场景召唤出来了。另一幅画《腊月》(1984)画的是两个在村口向遇的农民,穿着简陋粗糙的棉衣,以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招呼。孙为民的风景画和人物画好像都是发生在同一个场景,岁月流淌,乡情依旧,只有对农村怀有浓厚情感的人才能在这些简单的场面中表达出人道主义的情怀。
乡土现实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后,便开始向不同方向分化。发生在80年代中期的前卫艺术运动(85运动)对乡土现实主义形成最大的冲击。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引向城市,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中国的社会变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都市化伴随着工业化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农村也逐渐从人们关注的视线中消退。从表面上看,前卫艺术运动在主流上是照搬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但实质上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在艺术形态上对“85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反西方工业化时期的早期现代主义风格。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看,“85运动”和乡土现实主义一样,都是起于70年代末,盛于整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是体现在美术界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乡土现实主义的变化或分化反映出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与衔接。但从整体上说,乡土现实主义在逐步走向衰落。从变化上看,乡土现实主义更多的是接受了现代艺术中的原始主义观念,将乡土题材的某些精神因素与形式的追求融为一体,不再是如实记录现实场景,而是在形式中展现人的原初本性。在这方面,湖北艺术家尚扬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尚扬厦门市油画产业协会的成名之作主要以黄土高原为题材,但他沿袭的不是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的思路,他不是对现实的再现,他是以黄土和黄河为意象提炼出极为概括的形式,通过形式本身的张力高扬了一种本土文化的精神。尚扬能够从众多表现黄土和黄河的画家中脱颖而出,恰恰在于他不是再现题材,而是表现形式,但形式又不单纯是抽象的视觉关系,是在半抽象的形象上凝聚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因为在那些形象中黄土高原的人物形象特征和地貌生态特征都转换为形式的张力,直接通过视觉的感受唤起那种凝重而久远的文明意识。尚扬在80年代中期的作品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在抽象化程度上主要分为两类,稍早一些的作品较为写实,如《拉话》(1982)、《峪里》(1982)和《爷爷的河》等,这些作品都以黄褐色为基调,场景与情节都极为简略,从生活化的场景中又显然能感受到形式的潜在话语。如果与几乎同时在罗中立的《故乡组画》作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到,虽然两者都是变形,但罗中立的变形集中表现了农民的憨拙和纯朴,尚扬的变形则是强化地域形象中的文化特征与视觉特征,粗犷的笔触象征了地貌与形象的沉重,黝黑的色块则是沧桑岁月在肤色上的反映,非三度空间的场景构成强化出坚忍的生存条件。另一类作品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抽象,如《黄土高原母亲》和《老辈》(1984),人物形象经过变形处理,几乎与背景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不是形象的重叠,而是形式的类同和匹配,既使人感受到抽象的形式张力,又领悟到黄土文化的雄浑与粗犷。显然,尚扬不是情绪化地表现自我,是在研究了抽象艺术语言的基础上,对于抽象化的表现形式的一种自觉选择。在尚扬看来,人的问题是艺术表现的主体,他的黄土系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在于他不是简单地复制和修正视觉形象,而是突出了人在这种生存环境下的生命力,在抽象化的形式中凝聚了人的生命力,形式也就人格化了。
正当“85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乡土现实主义的最后一个浪潮却在东北兴起,虽然是姗姗来迟,却也如异军突起,从现代艺术思潮上看,东北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广廷渤的《钢水?汗水》在80年代初曾引起美术界的广泛注意,这种风格为现实主义绘画提供了一种新的样式,但同样以照相写实主义为背景,其精神的力度却远不及罗中立的《父亲》,倒是更像用现代艺术的语言来阐述文革的题材。但在“85运动”开始之后,东北的青年艺术家却能够为乡土现实主义注入新的活力,显然有其独特的背景。乡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影响到东北正好是“85运动”兴起之时,可以认为,学院式的再现乡土题材显然已失去了效力,而“85运动”中那种盲动的现代主义热情也不可能为相对封闭和滞后的东北艺术家所接受,因此一种学院基础上形成的折中主义风格便油然而生。东北乡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宫立龙和韦尔申都具有这种倾向。就像原始主义体现为乡土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一样,“85运动”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和理想,而在艺术的实践中,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样式成为85运动的一个显着特征。折中是对盲动与激进的制约。“85运动”的阴影并不能遮蔽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艺术总是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发展,即使现代艺术也是如此。从形态上来说,乡土现实主义仍然属于以学院为中心的现实主义风格,从伤痕美术到乡土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在题材上的转变,现实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东北的乡土画风实际上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对乡土题材的发现,但同时又是接受了现代观念,于是发生了现实主义的变体,即所谓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折中风格。基于中国学院艺术的传统和现代主义的困惑,这种变体的现实主义既是现实主义的延续,也是对前卫艺术运动的补充,甚至是现代艺术观念在现实主义艺术上反映出的积极成果。
韦尔申《吉祥蒙古》创作于1989年,也在同年的七届美展上展出,这一年的年初是“89现代艺术展”。现代艺术展既是对“85运动”的总结,也象征着“85运动”的终结。同样,《吉祥蒙古》也象征着乡土现实主义的终结。从1990年开始,“新生代”登上中国画坛,以学院为中心的现实主义风格完全转向了都市题材,而且这也是没有经历文革与知青命运的一代人,现实主义彻底告别了乡土。随后,中国社会快速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当代逐渐面对后现代主义问题,乡土现实主义也在市场经济中沦为一种标准的风情画风格,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已难有一席之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吉祥蒙古》已远离乡土现实主义,尽管它采取了乡土的题材,但其目的不是像陈丹青或罗中立那样在乡土题材中凝聚着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吉祥蒙古》在主题上是告别苦难,告别一个时代,但作者的真正动机是在这一象征性的传统现实主义题材上注入现代艺术的语言,不仅是中国农村本身正在告别过去,而且依附于这一题材的艺术也在告别自身,进入现代。从形式上来分析,《吉祥蒙古》在构图和造型上都有一种几何形的结构,作者不是像原始主义那样把牧民的乡土特性作原始意味的变形,而是结合立体主义的观念和学院艺术的造型基础,将演变乡土题材中粗拙转换为厚重体积感与平面化结构的结合,韦尔申的这种手法使人想起同样从立体主义演变过来的法国画家巴尔蒂斯,虽然他们的题材与观念完全是两回事,但这也证明,韦尔申更多的是关注形式和语言,乡土题材成为他实现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观念媒介。在“85运动”的后期,一部分艺术家在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之后,开始了向内转的过程,结合中国的现实与文化,创造出真正中国式的现代艺术。在这其中,徐冰和吕胜中代表了激进的一翼,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观念艺术相结合,直接进入当代国际艺术的主流形态。而像韦尔申等人,则代表了保守的一翼,他们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循序渐进地把中国现代艺术的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相结合,创造出自己的话语形式,但是这种结合也不可避免地结束乡土现实主义的时代。
韦尔申《吉祥蒙古》创作于1989年,也在同年的七届美展上展出,这一年的年初是“89现代艺术展”。现代艺术展既是对“85运动”的总结,也象征着“85运动”的终结。同样,《吉祥蒙古》也象征着乡土现实主义的终结。从1990年开始,“新生代”登上中国画坛,以学院为中心的现实主义风格完全转向了都市题材,而且这也是没有经历文革与知青命运的一代人,现实主义彻底告别了乡土。随后,中国社会快速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当代逐渐面对后现代主义问题,乡土现实主义也在市场经济中沦为一种标准的风情画风格,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已难有一席之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吉祥蒙古》已远离乡土现实主义,尽管它采取了乡土的题材,但其目的不是像陈丹青或罗中立那样在乡土题材中凝聚着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吉祥蒙古》在主题上是告别苦难,告别一个时代,但作者的真正动机是在这一象征性的传统现实主义题材上注入现代艺术的语言,不仅是中国农村本身正在告别过去,而且依附于这一题材的艺术也在告别自身,进入现代。从形式上来分析,《吉祥蒙古》在构图和造型上都有一种几何形的结构,作者不是像原始主义那样把牧民的乡土特性作原始意味的变形,而是结合立体主义的观念和学院艺术的造型基础,将演变乡土题材中粗拙转换为厚重体积感与平面化结构的结合,韦尔申的这种手法使人想起同样从立体主义演变过来的法国画家巴尔蒂斯,虽然他们的题材与观念完全是两回事,但这也证明,韦尔申更多的是关注形式和语言,乡土题材成为他实现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观念媒介。在“85运动”的后期,一部分艺术家在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之后,开始了向内转的过程,结合中国的现实与文化,创造出真正中国式的现代艺术。在这其中,徐冰和吕胜中代表了激进的一翼,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观念艺术相结合,直接进入当代国际艺术的主流形态。而像韦尔申等人,则代表了保守的一翼,他们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循序渐进地把中国现代艺术的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相结合,创造出自己的话语形式,但是这种结合也不可避免地结束乡土现实主义的时代。